
文/采访:btr
照片由黎紫书本人提供
继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后,马华文学领军人物黎紫书的短篇小说集《野菩萨》近日在中国大陆出版。全书收录的13个短篇多为获奖之作,它们风格各异,写“异化的国族”,也写“错位的寓言”(王德威语)——无论是寓言般的国族书写还是俄罗斯套娃式的元叙述实验,无论是人称变换还是语言创新,短篇小说都是黎紫书的实验之地,也是她的丰收之地。近日,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对黎紫书进行了专访。
《野菩萨》收录的13个短篇创作于不同时期,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在这十多年里,您对于“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认识有何变化?
这书里的作品说是写在十二、三年间,其实只是分成两个阶段。前面几篇写在我的“后参赛时期”,后面的则写在我的“新创作时期”,两个阶段之间隔了一个相当长的空白期。我在那为时约莫六年的“短篇小说空白期”里,写了许多微型小说和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些作品以后,我忽然重新生起创作短篇小说的兴致,并且觉得这些年醖酿的题材和故事似乎已经成熟了,于是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另一个创作时期。
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对短篇小说创作自然有了些不同的想法,包括我所关注的主题、语言和审美追求的变化等等。这些改变不仅仅是因为“参赛与否”的考量,也因为我在长篇和微型小说的书写中,对不同篇幅的小说体裁有过认真的思考。我必须想明白“短篇小说何以为短篇小说”,也就是要说服自己何以短篇小说不可被取代,因而我得给自己心目中的短篇小说建立一套有别于中长篇和微型小说的审美标准,如此我才可以把短篇小说创作继续进行下去。
至于这属于短篇小说的美学标准,目前我还在探索中,尚未有一套清晰的概念。当然我十分怀疑这是否最终真可以成为某种可以被阐述的理念,抑或它根本只是某种意识或直觉。
我对自己写的各个体裁,基本上都给它们设想了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你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其他?”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以这个体裁书写?”如果说每个体裁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我就得找出这些理由,然后才能选择适合的体裁去表现我所要表达的想法和意见。在我,那“存在的理由”里最重要的是各种体裁之所以不可被别种体裁取代的原因,它们各有其美学标准和要求,也因此我以不同的体裁表现不同面向的“我”,才会有这种各体裁文字风格迥异的情况。
作为一个出生在怡保、曾旅居伦敦和北京的小说家而言,对于写作的语言有怎样的自觉?是否会刻意吸纳或拒绝“外来”或“别处”的语言?
我接触和学习的语言越多,我越觉得语言比我想像的更迷人。我计划中的下一部长篇,就要以“语言”作引子。我热爱中文,但对其他任何语言从未有丝毫排斥,总觉得每认识一种别的语言,必然会使得我对自己的语言回顾及反思,也让我一次一次地意识到中文书写还有其他更多的可能。
过去我曾汲汲要寻找一种马华的语境,而经过好些年的尝试与实践以后,我发现“寻找”实在是无望的,因为在文学层面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经过选择和加工的语言,因此现在我更相信自己该“创造”马华的文学语境。而“外来”或“别处”的语言可以成为借镜,甚至能作为材料,加入到此一创造的过程里。
那么您作为一名马来西亚的华语作家,是如何看待自身的“离散”处境的?
“离散”一词太常被套用在马华作家身上了。但我怀疑今天我们这一辈和我以后的马华人,还有多少人真会自觉“离散”。我以为那首先得自觉有个“出处”,有个原乡。但比起我们的先辈,有这种(文化)原乡意识的马华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纵有如此意识,这意识本身也已经一代比一代稀薄。其实我十分好奇,马来西亚这些年也出了好些以英语写作的好手,就不知道他们在是不是也会被人以“离散”标签,也会一再面对这种问题?
真要探讨的话,因着马来西亚的种族和教育环境,整个情况要比我们想像的复杂。但我更在意的是“探讨”本身的意义,也许它更适合作为学院里研究的课题。对于已经不再感觉“离散”的人而言,这探讨就像是我们在向一个应因生存需要,已经从陆地生物演化成海洋生物的什么动物,追问它的想法和感受。
您提到在马来西亚有不少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如Tash Aw(欧大旭)或Tan Twan Eng,他们在国际文学界皆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华语作家同他们之间有所交流吗?您如何担待马来西亚的英语文学?
就我所知,马华社会中的华语和英语写作者是两个圈子的人,彼此极少交流,甚至也互不相识。我倒是透过台湾联经出版公司读到了欧大旭的著作,而据说他也透过出版社拿到了我的《告别的年代》。两个马来西亚华人作者透过台湾的出版社,又在分隔两地的情况下初次接触到对方的作品,这感觉真怪异。现在我倒是更相信(也很期待)有一天这两批馬华写作人会在海外被撮合,在某个场合中正式相遇与对话。

您最近读过哪几本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中文小说?能否比较一下自身的写作与上述小说之异同?
过去半年我读过的中文小说,只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和韩少功的短篇集《鞋癖》,两本都不是新作。其他读过的书,多是翻译或英文小说,也有散文与杂文集子。这些年我读的中文小说实在很少,事实上是我阅读的速度越来越慢,所以会倾向于选读“中文世界以外”的作家写的书,想看看别人的思维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在上述两本中文小说中,我比较喜欢写法朴实的《我与父辈》。那实在不是什么大胆的新颖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写法传统,语言文字格调也不太高。但也许是年纪大了,阅读的口味会变淡,比年轻时懂得体察细微之处的美,不太容易倾倒于太强烈太张扬的作品。《我与父辈》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写父辈那一代人朴素真挚的人情,还有那简单的生活和坚韧的人性,读来十分动人。要说比较,我觉得我自己的写作,甚至是我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人们的写作,不管我们写作技巧多好,也不管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多华美,都不太可能再写出这种能人情味来了。
在《野菩萨》的后记里,您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风格”的作者。在您看来,什么是风格?若文字风格可以被读者一眼识出,对您而言,是好还是坏?
其实我说自己“没有风格”是不正确的。我固然向往当一个没有风格的作者,但人不可能没有局限,尤其年纪渐长也就难免逐渐定型。一个人再怎么求变,但他基本的的价值观美学观艺术品味和生活态度都在那里了,那么他写的东西势必就包含这些元素。
我能做到的仅仅是为以不同的笔风写不同的体裁,偶尔也用上不一样的形式,但阴暗啊冷酷啊悲剧性啊,都是我不可能甩掉的。那些可以说是我的“信仰”,我的神在我的书写里,祂不是能换的。
一直以来,我阅读时评定作品好不好,都不把“有没有作者的个人风格”计算在内。对我来说,文字风格能不能被一眼识出,这事无关作品的成败和优劣。要是作品没写好,再强烈的文字风格也不能挽回;相反的,作品要是写好了,文学的力量在那里了,则里头有没有所谓的个人风格又有什么重要呢?
您是如何看待虚构作品之中“真”与“假”的边界的?
我以为这“真实世界”里所有人与事情,一旦落入文字,被文字所描绘和叙述,它就会落入某种意义上的“虚构”里。若奉文学之名,尤其是小说,那更是再无所谓边界了。小说是一种把所有真实写得“像假的一样”,却同时又可以把假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的文体。但归根究底,小说的本质非关“真假”,它本是一种“说故事”的艺术,我们要的是故事被说出来时所放射的能量。好的小说即便说的是一个明摆着虚构的故事,也能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真实”的压迫。
但我不是对每一种文体都如此看待,比如说我不支持“虚构散文”,不赞同散文也享有与小说同等的虚构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划分小说与散文的区别的基本准则。我会想:要如此虚构的话,我为什么不写成小说?
您从前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也用不同的笔名写犀利的时政杂文。有许多作家都是记者出生的,如安东尼奥·塔布其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您觉得做记者这段经历对于身为小说家的自己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让我来虚想一下,要是没当过十余年的记者,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这段经历也仍然写作,那么我会在写什么呢?
我知道那是肯定不一样的。我很可能不会在写小说。当记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它训练我去聆听,观察和怀疑,并且从中发现故事。这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而言,当然是很宝贵的经历。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从事媒体工作让我在写作时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以致我的写作有一种明显的“倾诉”的意向,而这种对阅读者的高度察觉,也使得我特别喜爱以第二人称书写。
接下的创作计划是继续写短篇,还是已有新的长篇构思?
目前手头上正进行着两个短篇,估计完成以后会再一次离家,安排另一次较长的“出走”。我会试着在这次出走期间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目前构思已经初步完成,尽管我知道它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变形。但“开始写”毕竟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我很清楚若我生命中还有下一个长篇小说,它肯定不会在马来西亚写成。因为只要我人在老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特别多,人在事情当中,心难平静,而且我的时间也会被切割得太碎了。
请介绍一下您的写作过程?有固定的时间、提纲或某些具有仪式感的安排吗?
我缺乏计划和组织的能力,但我有酝酿和等待的耐性。我写作很随性,除了一两杯咖啡和随机的音乐以外,再无什么其他“仪式”。我一般会在白天写作,晚上心神就很难留在写作上。反正三几天没写什么就会焦虑,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在消退。
写作对于您,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写?
这问太大了,我一直不愿去想它。对于我来说,写作关乎表达与沟通的需要,也是一种能力。我的宗教会告诉我,那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珍惜这种能力,我可以七天不说一句话,但做不到三天不写一个字,因而它于我是比口语更重要的表达的途径。但我说不出来“写作是我的生命”或是“它是我的全部”这种话,我只能说它多少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可是它不能凌驾生活本身,这点还是很分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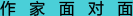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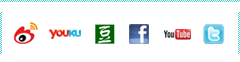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