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雷蒙•鲁塞尔?每一个想要向本国读者介绍雷蒙•鲁塞尔的人,都可以像约翰•阿什伯利一样说:鲁塞尔对我国读者来说非常陌生,但在法国本土也并没有更多人知道他。五十年过去了,随着阿什伯利和福柯以及“新小说”诸将的研究和推介,鲁塞尔获得了越来越多关注,他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在慢慢滋长,但对于大众来说,鲁塞尔仍然是那个天才而怪诞的有钱人。
对于受到鲁塞尔极大影响的科塔萨尔,聂鲁达有酷评如下:不读科塔萨尔的人注定会完蛋,不读他是一种严重的疾病,迟早会出问题,就像是,一个人永远没有品尝过桃子的滋味。不读鲁塞尔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但读一读鲁塞尔,我们一定可以学会不少东西,品尝到一种奇异水果的滋味。
第一层:替身
鲁塞尔的人一直盖住了他的作品,就像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La Doublure(法语中“衬里”或者“替角”的意思)所预示的,衬里反而盖过了衣服,替角的光芒掩盖了主角。人们关注他的各种怪癖和轶事,但并不怎么读他写的书。
当然,这是因为鲁塞尔太难懂了,但那些能够感受到他作品魅力的人,会变成他疯狂的拥趸,会在剧场里为了捍卫他的作品而跟俗众们对骂、打架,比如布列东、艾吕雅、阿拉贡、德斯诺斯,以及他们那些超现实主义的同志们;或者,即便不那么疯狂,也会受到他巨大的影响,比如杜尚,鲁塞尔让他从后印象派那里转向了他自己后来的道路,他的著名作品《被求婚者们扒光了的已婚女人》直接源自鲁塞尔,贾科梅蒂的早期作品也受到了鲁塞尔的重大影响。还有一些人,比如考克多,甚至会避开他,反抗他,怕自己被他的影响完全覆盖,不再是自己。在这些最初的接受者之后的“新小说”和“乌力波”,也从鲁塞尔那里获得了方法论的启迪。
鲁塞尔的文学宇宙太过奇特,要搞清楚作品的谱系,还得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雷蒙•鲁塞尔1877年1月20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庶家庭,父亲是成功的交易人,母亲家中也颇有钱财(他外公是巴黎公交总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出生地在巴黎的高档街区玛德莱纳地区(里兹大酒店和名店云集的圣奥诺雷区),坏草大街25号,这条街的9号住着普鲁斯特一家,两家人的圈子不无交集,后来给普鲁斯特的处女作《欢愉与时日》创作插图的女画家玛德莱纳•勒迈尔也给小鲁塞尔画过肖像。衣食无忧的小鲁塞尔也同样醉心于文学和艺术,他的父母觉得他有音乐天分,就让他进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他的成绩也证明了,父母的眼光没错,他能用最高的技巧演奏李斯特和肖邦最难的作品,教授们都啧啧称奇。虽然他两次年终比赛分别拿了次优和最优,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以音乐为志业,因为他尝试了写诗配合自己作的曲子,比较起作曲和作诗,他觉得,“音乐总在反抗”,诗行的到来更加容易。
1894年,他父亲去世了,给他母亲和几个孩子留下了4000万金法郎的遗产,遗产的代理人是米歇尔•莱利斯的父亲,两家本就是故交,这一来,两个年轻人走得更近了。年轻的鲁塞尔被写作的激情占据着,这一年,17岁的他完成了长诗《我的灵魂》,20岁时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写出了长达5586行的长诗《视》(La Vue)。1989年在一个家具货仓里发现了九箱鲁塞尔的手稿,其中有两部是他写作生涯的前十年创作的两部长诗,每部都有七、八千行。写作给了他莫大的满足,他承认,在他写作《视》的那几个月,他感到了一种“超常强度的宇宙性的荣耀”,这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在写作中他感到自己就是太阳,自己注定会被世界和众人仰慕,他甚至不敢拉开窗帘,因为他觉得,如果拉开一丝缝隙,他的光芒“会一直照射到中国去”。
可实际上,并没有出版社要出版这部大作,于是鲁塞尔花钱在出版“高蹈派”诗人诗集的Lemerre出版社自费印行了处女作,他自信满满,觉得没有作家能比他更优越,公众和评论界马上就会拜倒在他的天才之下。结果是残酷的,这本书的出版毫无反响。这时鲁塞尔才发现,他预期的天崩地裂并没有发生,世界照常运转,巴黎还是之前的样子。巨大的反差和失望让他全身出满了皮疹,几乎精神崩溃。家人不得不找来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皮埃尔•雅奈(Pierre Janet)为他治疗,后来雅奈把鲁塞尔的案例写进了他那本《从焦虑到狂喜》(De l’angoisse à l’extase, 1926)。这位医生认为鲁塞尔智力超常,判断力准确,只要不涉及写作这件事——在他看来鲁塞尔并无文学天才。
但鲁塞尔坚持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学天才,是新的维克多•雨果。他觉得,他一生荣耀和幸福的顶点是《视》,他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重新体验当时的感觉。他之后的写作更多是为了让人们去注意到他最初的杰作。他觉得,可能诗歌太难以进入,于是他要像雨果那样也写一些小说,但《非洲印》和《独地》又失败了,书根本就卖不掉。他想要自己去找读者,就花钱把小说刊登在《高卢人》杂志上,但也没什么效果。
历经失败的鲁塞尔想,可能改编成戏剧上演会成功,埃德蒙•罗斯当也告诉他,《非洲印》这个小说可以改编成很好的戏剧。于是他就自己改编成戏剧去上演,结果仍然是没有反响,没几次就停演了。到了1912年,他重新去上演这部戏,这一次倒是有了反响,公众认为这是个大丑闻,有人把它和《乌布王》相比,但总的来说没有人理解这部戏。杜尚的名作就是从这里获得了灵感,但公众并不理解这部太过荒诞的戏剧,鲁塞尔不得不自己掏钱在戏剧杂志上发文章捍卫自己。
第二次改编的尝试是在战后,1919年,鲁塞尔怕上一次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不会把握观众的心理,就请了当时名盛一时的剧作家皮埃尔•福隆戴(Pierre Frondaie),花了三年时间去改编,场景、服装和演员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结果却是更大的丑闻。不过,这一次起码有人站在他这一边,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剧场中和起哄的人群对骂,观众里有人对他们喊:“再加把劲儿啊,巴掌托儿们!”,德斯诺斯迅速回了一句妙语:“我们要是巴掌托儿,那你们就是脸!”
一次次的失败让鲁塞尔愈加失望,公众知道他,谈论他,无非是因为他的怪异生活方式,比如他一天只吃一顿,从中午十二点半到傍晚五点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一起解决;再比如他发明了一个类似现代房车的豪华旅行车,到罗马的时候连教皇都派人去看,墨索里尼则是亲自去参观。此外,他旅行几乎不出门看任何东西,就是在房间里写作。
鲁塞尔不希望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怪异而富有的文学爱好者的形象,但他所有的努力(加上他奢侈的生活方式)花掉了他大半家财,却并无效果。最后他印行自己最后诗作《非洲新印》的时候,附上了自己最初的作品《我的灵魂》,但名字换成了《维克多•雨果的灵魂》,里面那个写出伟大作品的人的名字,本来按照押韵应该是“鲁塞尔”,但他硬生生改成了“雨果”,这时他大概使用了过多的巴比妥,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幻了。这也可以解释他最终的死亡,他选择死在1933年的7月14日,这大概是为了像雨果一样享受到国葬的礼炮,另外他最早的作品《我的灵魂》是在七月出版(paru,出现)的,可能他也想让“我的灵魂”在同样的月份离去、消逝(disparu),像“维克多•雨果的灵魂”一样享受普遍的荣耀。
他死前留下有待印刷的最后一本书,《我怎样写作我的部分作品》,这本书是一个钥匙,他把钥匙留给世人,让他们拿着钥匙去试着打开自己的迷宫,而他自己,这个过于引人注目的替角,决定就此退场,让作品这个真正的主角留在舞台上,留在人们的视线(la vue)之中。
第二层:文本身
要考察鲁塞尔的文本本身,应该从他最看重的、最早出版的作品开始。和鲁塞尔的其它词汇一样,La
Doublure这个书名具有双重含义,“衬里”或者“替角”。鲁塞尔往往选取的是不那么常用的意思,这里也不例外,这首长达五千多行的亚历山大体长诗写了一个只能当替角的三流演员和他情人的故事,在尼斯他们碰上了狂欢节。情节?可以说几乎没有情节,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就是在详细描述狂欢节上的花车和面具,足足有四千六百多行!
这样的诗集,也难免当时杂志上的评论者一个说“几乎难以理解”,另一个说“非常无聊”,和当时的风尚相比,鲁塞尔的长诗确实难以索解。为什么他在写作这样一部诗作时,感到了一种“超常强度的宇宙性的荣耀”?这是一种“被占据的”写作状态,一种对“看”和视觉的着迷。确实,在鲁塞尔的作品中,五感都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视觉是统治性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头的著名段落所说,求知是自然而然的欲望,我们从感官中获得的快乐便是证明,即便是没有什么用处,即便并不是要以此去做什么,我们也喜欢这些快乐,而视力给我们最多快乐,因为它最能让我们获得知识,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
因此,即便这种视觉、所见和视力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种观看和获知的愉悦。但“视”不仅仅可以用来获知,也可以用来创造:创造差异,以这些差异创造事物和世界。鲁塞尔在《视》这部诗集里的三首长诗,情节可以说是点缀,真正详细描写的是三个场景,第一首《视》用2000多行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一个笔架上的透镜里看到的海滩场景,第二首《演奏会》用1000多行描写了一个旅馆信纸抬头上的演奏会图景,第三首用1000多行描写了一瓶矿泉水上的源泉图案。这种过于细致入微的描述热情让一般人难以承受,这本诗集足足卖了五十多年,直到1953年才全部销售完,两年后,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Le
Voyeur)出版了,这部向鲁塞尔致敬的小说,本来的名字是La
Vue(《视》),跟鲁塞尔的诗集名字一模一样。罗伯-格里耶开始的小说(不仅仅是《窥视者》,还包括《嫉妒》),都是鲁塞尔式的详尽描述,仿佛一架不知疲倦的摄像机,永远在观看,永远在记录,仿佛这种观看本身,就足以给作者和读者足够的满足。
但同时,鲁塞尔的写作并非单纯的观看和记录,也是发明和创造,创造新的事物,新的事件,新的世界。如果说前面两部长诗还更多是对现有世界的描述,后面的两部小说则更多是发明和创造。前一部《非洲印》是发明场景,是一场虚构的盛大表演,后一部《独地》更是生活和器物的大发明,佩雷克的《生活使用指南》直接与此相关,但鲁塞尔的作品更孤独,更极端。
《非洲印》当然是一个文字游戏,Impressions
d’Afrique,可以是“非洲印象”的意思,但也是Impressions
d’à fric的声音,这里Impressions就是同一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印刷”,整个的意思是“掏钱印刷”,相当于Impressionsà compte d’auteur,“作者自费印刷”。没有出版商看上鲁塞尔的作品,他一生都是自费印刷,所以到了出版第三本书的时候,他干脆用了这么个名字自嘲,《非洲印》既是非洲印象,也是自费印刷。
鲁塞尔为了写这本小说确实在非洲周游了一番,但他几乎不出旅馆的门,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房间里埋头写作,然后去下一个地方。就连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他们的船沉没了,当地土王活捉了他们,他们就被关起来,等待来自欧洲的赎金,期间他们为了自娱,就排练了一场联合汇演,等待被释放的那一天好好庆祝一番。
这又是一场演出和狂欢,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写实,不是来自作者旅行的“印象”,而是通过作者的发明、因为作者(à compte d’auteur)而产生的“印象”。这也正是杜尚和贾科梅蒂从鲁塞尔那里学来的东西,杜尚说,本来他还在后印象派那里打转,看了鲁塞尔这本小说改编的戏剧,他突然明白了,创作可以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印象不需要来自现实,它们可以来自梦幻和想象。于是,当博纳富瓦在法兰西公学讲授诗学之际首先引用贾科梅蒂来说明诗与艺术的关系之时,历史完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思想从诗人到雕塑家然后又回到了诗人。
考克多也因此把鲁塞尔称作“梦幻的普鲁斯特”,阿拉贡则给了他更高的位置:“梦幻共和国总统”。作为“总统”,他代表着梦幻对现实的权力,诗学就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展开了一个古老的维度。超现实主义者们向鲁塞尔致敬、欢呼:伟大的鲁塞尔,再给我们更多的梦幻吧,再给我们更多之前未曾存在的东西吧!
于是写作不再是去描述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去想象和发明未曾存在的事物和世界。在这样的影响之下,科塔萨尔完成了他最疯狂和怪诞的一本小说:《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鲁塞尔这个发明家,他发表了一个数学定理,构想了新的织毯机,在国际象棋领域做出了足以留名的创造,他的构造天才和构造方式秘密地影响着文学史,但在生前,他一直是那个不成功的作家。
最后出版的作品《非洲新印》是鲁塞尔最后的自嘲,疯狂的写作机又要自费印刷了。这一次他回到了诗歌,这是他最后也最伟大的作品。这一次的革新直达形式本身,他用了五层括号来不断偏离又回到主题,这首长诗分成四首每首长达几百行亚历山大体诗行的“歌”。从语法上来说,每首歌就是一句话,但不读到结尾,绝对无法知道这句话究竟在说什么,因为中间的几百行之内,插入了数层括号,括号里又有括号,然后又还有注释,有注释处的诗行和注释开头的诗行押韵,注释末尾的诗行再和之后的正文第一句诗押韵,所以没有可以掠过的部分,必须一个个注释、一个个括号读过去。
鲁塞尔自己都觉得,这对读者来说可能太难了。他想过用不同颜色来印不同括号和层级内的文字,但在当时,这可是件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花费会大到连向来对印书一事挥金如土的鲁塞尔都觉得难以承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折腾了这么多年,自己也终于有点吃不消了)。这个构想直到2004年才由AL
DANTE出版社实现,在此之前,面对这些远远超过康德或者普鲁斯特的长句,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反复阅读,因为十个手指头已经不够,加上脚趾也远远不够,鲁塞尔的这些长句,只有百足虫可以轻松自如地阅读。
所有这些括号、注释、插入再插入,这一切意义何在?那59幅匿名请Zo刻制的、与正文时常脱节的插图(鲁塞尔请了私家侦探所去联系他本来认识的Zo,这位木版画家是在不了解诗集如何以及作者是谁的情况下,按照59条书面指示创作了59幅版画),又是为了什么?鲁塞尔的目的是,让这些文本和现实尽量脱节,通过一道道括号和注释,通过插图的撕扯和偏离,让读者迷失于逻辑和语言之中,这时只有逻各斯自身在起作用。
这座逻各斯的迷宫可能需要一把钥匙,鲁塞尔最后留给了我们这把钥匙,这就是那本作者死后由友人莱利斯帮助印行的《我怎样写作我的部分作品》。在这本书的开头,鲁塞尔做出了很大的承诺,一直以来都有人问他究竟是怎样写作他那些费解的作品,他许诺他将揭示一直以来使用的“流程”(le procédé)。这个流程在我们前面对双关词的解释中已经揭示出一部分特征,但用下面几个例子能更好地说明。
A.歧义的形似。鲁塞尔一直会用两个相同或几乎完全近似的句子,一个用来开始叙述,一个用来结束这个叙述,比如他的一个故事就用了下面这两句:
1. Les lettre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billard(旧弹子桌边缘上的白粉笔字)
2. Les lettre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pillard(老劫匪帮众身上的白人的信)
所有词都有双重含义,在两个句子里完全不同:lettres(字/信),blanc(白粉笔/白人),bandes(边缘/帮众),vieux(旧/老),billard(弹子桌)/pillard(劫匪)。
前面的词,词形完全相同,最后的billard和pillard也是近乎相同的音似,是词形变换的结果。
B.音似。鲁塞尔会从他身边的一切获得文本的来源,比如,从一首老歌《我有好烟草》里他得到了一个故事的几乎所有元素。那首歌谣的开头是“我的烟盒里有好烟草(J’ai du bon tabac dans ma tabatière),从这句他得到了“亚光的玉条波晨曲有低三度”(Jade cube onde aubade en mat a basse tierce)。两句在法语中读起来音似,但意思完全不同;这首歌的第二句是“你可得不到”(Tu n’en auras pas),从中鲁塞尔得到了“金沙丘有足迹”(Dune
en or a pas)。一首平常的歌谣,经过鲁塞尔的变形,就成了一个怪诞的故事。
这样的变形有什么意义?莱利斯认为,鲁塞尔的叙述的生成回到了神话生成的最古老方式,神话来自逻各斯,这逻各斯不是逻辑的逻各斯,而是无法溯源的语言。
C.嵌套。通过不断地插入和嵌套,一层又一层的括号,鲁塞尔把语言打回原始的晦涩状态,其中有逻各斯,但不是我们通常的逻辑。
鲁塞尔的种种方法可以说是视觉和听觉的混合,通过声音的相同、相近和变化,达到视觉上的变化。这是音乐家鲁塞尔和视觉饕餮鲁塞尔合谋之下的“词与物”的“变形记”。
我们也许以为,鲁塞尔最后的文本是一把钥匙,一种揭示;
我们一直以为,卡夫卡最后的遗嘱是一场焚烧,一种掩藏。
可正如向上与向下的道路本为一条,揭示之道就是掩藏之路。卡夫卡明知布罗德绝不会毁掉自己的手稿,还是把它们交付给他,让他在自己死后毁掉它们,真的可以说布罗德背叛了他的遗嘱吗?鲁塞尔明知道,自己的解释并不能让人更理解他的著作,他还是留下了这把钥匙,他真的是希望帮助我们走出迷宫吗?或者毋宁说,两者留下的,都只是一个踟蹰犹豫的姿态?鲁塞尔死在爬往房间门的地上,我们无法知道,迟疑的鲁塞尔究竟是要打开门,还是要锁上门。有的作者可以选择生死,有的不能。至于文本,文本的生死取决于什么或者谁?
如果钥匙和线团并不可靠,我们只能:独自走入迷宫,去看,去听,去获得看的能力,去夺取空空的透镜,因为文本生成的“独地”(locus solus),也正是存在与生命生成、变化的唯一场所。
Raymond Roussel :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Pauvert, 1963-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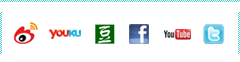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