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翊云,欧宁摄,2012年7月2日,旧金山]
欧宁:你曾经在爱荷华大学修读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在某次采访中曾提过有两位老师James Alan McPherson和Marilynne Robinson对你很有影响,后来你成了作家,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这个课程,我想请你具体讲一下美国的这个课程,你在爱荷华大学时老师是怎么教的,对你的写作在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后你自己当了老师,又是怎么教学生的?
李 翊云:因为我以前没有写作背景,所以我去读了爱荷华的这个课程。我觉得在爱荷华有两种老师,一种老师是教你写作技巧的,另一种是教你怎么阅读的。我刚进去 的时候有过两个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都是作家,其中一个很注重技巧,比如他会说你这个开篇不好,你这篇文章里用哪句话可以开得更好一些,或者你讲述故事 的顺序有没有关系,你先讲这个东西再讲后面的,读者已经失去兴趣了,他很讲究技巧,而且也很讲究语言,比如一句话里头这个字应该拿出去,这个老师的头三堂 课真是令我受益匪浅啊,上完这三堂课接下去这学期的14节课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他总是重复地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技巧是应该学一些,但是像我提到的James Alan McPherson和Marilynne Robinson,他们就不怎么讲究技巧,主要教你怎么读,尤其在Marilynne的 写作课上,她觉得学生习作再怎么也是练习的作品,她会从那儿引伸到一些艺术史、哲学史或社会学的知识,她会讲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最终是最重要的。我 觉得写东西,你写到一定程度,技巧的东西会写到的,如果没有眼光只有技巧,故事可能会写得很完美,但没有任何生命力在里头。我最感谢这两位老师的是他们从 来没有跟我讲过你应该怎么写东西、不应该怎么写东西,他们主要是教我看谁的书、怎么看。
欧宁:一般都会要求学生交一些习作是吗?也有一些经典作品分析?
李翊云:其实我们在爱荷华的时候主要是交一些习作,因为那个项目叫做Studio Program,主要是工作室为主,也有读的,但是很少,主要是学生交习作然后大家讨论。但是因为Marilynne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我估计是很Top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会讲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有一年她讲了一学期的《圣经》,有一个学期在讲《大白鲨》这本书,我觉得这个很受益。
欧宁:我看美国很多作家都上过这个课,在美国文学生产的这个系统里面,这是养成作家的很关键的一环,你上过这个课,今天也在教,你是怎么教你的学生的?
李翊云:我的学生都是很年轻的、想成为作家的,我一般也会教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因为技巧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工具,不过因为我自己的出版史也很短,很多时候我 主要还是教他们怎么读书、读谁的书。年轻的一代嘛,总是想成为最年轻最热门的作家,都很有野心,我想让他们知道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版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到了那儿写的不好还是不好,我教他们读很多老一代作家的东西,主要是教他们读书。
欧宁:有没有编辑这方面的课程?
李翊云:我们没有,我跟几个很好的编辑合作过,我觉得编辑需要的是另一个方面的天才,跟写作不太一样。我还在学编辑,跟着他们学,怎么改人家的东西和怎么改自己的东西。
欧宁:你是个作家,经常和编辑一起合作,同时你也是文学杂志A Public Space的编辑,能不能分享一下,作为作家,你和编辑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作为编辑,你又是如何和作家合作的?
李翊云:有两个编辑对我帮助很大。一个是《纽约客》的小说编辑Cressida Leyshon,有时候我给她我的作品,她不会说得很清楚哪儿不好,她会说“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干这件事情”。最经典的例子是他们出那个“Twenty under Forty”( 20个40岁以下的作家)专题的时候,我的小说,就是《天南》翻译发表的那篇《逃避之道》(The Science of Flight),有讲到一个年轻的女的去英国独自度假,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Cressida正好是个英国人,她很逗,说在英国那段很无趣,建议我把这段旅行拿出去不要放在故事里,当时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主要就是写那段旅行,她觉得写得不好,对英国人来说更无趣,这是个很极端的编辑。后来我重写了,我发现在英国的那一段不是很重要,在去英国之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去才是最有意思的,重写之后她说很好。和她有很多次来回,刚开始时是大段大段的,后来就针对一句话来回五、六个电邮,讨论她觉得应该那么写我觉得应该这么写,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个是A Public Space的主编Brigid Hughes,她总是问一些我没想到的问题,最基本的。也是那篇《逃避之道》,比较悲伤忧郁的一个故事,我也给她看了,当时在纽约一个公园里她就问我,“你想过这个女孩什么时候最快乐吗?”她 问的时候我就想,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她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她说我告诉你我觉得她和两个同事吃午饭的时候的交流是最快乐的,她说了以后我就又重新写 了。这样的编辑总是看到我的盲点,他们训练有素,看到了以后马上就会指出来。最近我看了一个很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我看了她的一个故事,写的是密西根的小 镇的故事,比一般的年轻作家写得好,隔了两个月我们回去看发现有很多问题,虽然写得好,很多地方都不合情理,比如她有句话,酒吧的招待是这个镇上唯一的女 同性恋,我和主编在编的时候就想如果她是唯一的女同性恋,她为什么要宣布自己是女同性恋,尤其是在一个很保守的小镇上。我们就问这个女孩,她说也没有想 到,所以我列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一个男的婚外恋跟这个女同性恋生了孩子,我就说你告诉我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谁勾引了谁,因为写东西的时候很快就带过 了,所以我列了很多问题,她就改了一稿,第二稿比较差,明显看出来她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但又出现了新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我又给她列了一大堆问题,这样 三、四稿以后问题就没有了,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就定型了,没有不通情理的地方,但故事成型以后语言就很差了,我就说这还不如最开始的那一稿好。最后她改好 了,但是我们没有定稿,我就说因为已经来回两个月了,你休息两个月,两个月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
欧宁:你同时是作家和编辑,你对现有的文学杂志有什么看法?
李翊云: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特点吧,就像出版界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大家写不一样的东西,有不同的风格。像《纽约客》,历史很悠久,他们有很严格的Fact Checking(事实核对),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收益的。我在上面发表第一篇小说,你记得九十年代有一个广告说“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吧,我当时的其中一个人物就是引用了这个广告,然后编辑就说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广告原来的录像,我们想看一下,我说这个我就做不到了。我觉得他们对故事的严谨和尊重的态度挺不一般的。Granta每一期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A Public Space恰好不做主题,因为做一个主题你总会有别的东西特别想发,没有明显的主题但是会有潜在的主题,比如第15期,第一篇像是文学评论,讲一个叫达达的精神病人,他喜欢走,可以走很多路,所以我们配图的部分就是游牧民族,会有潜在的联系但不明显。The Paris Review现在有很多非虚构的文章,不同的杂志会有不同的读者群,McSweeney’s可能年轻的一代比较喜欢。
欧宁:你对《天南》怎么评价?
李翊云:我觉得《天南》当时拿到的时候还是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以前看的都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些杂志,《天南》在我看来跟美国和英国的杂志更接轨一些。
欧宁:你是2013年布克国际奖(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评委,你要评选自然要看很多很多参选的书,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工作,跟你的个人写作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阅读给你一个关于当代英语文学的怎样的印象?
李翊云:去年夏天我看了350本书,因为去年夏天我是两个文学奖的评委。布克国际奖和布克奖是不同的,布克奖评的是年度最佳的一本书,而布克国际奖要求评委看的都是成名作家一生的作品,大约要看同一个作家的五、六本书。我觉得看任何一年、一个阶段出的书,出版业就像一座金字塔,好的书就那么几本,在顶尖,但不可能没有下面这些书支撑着。像我们去年评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五个评委对最好的50本的感觉其实是很一致的,不好的书你看两页就知道了。我比较喜欢布克国际奖的工作,因为要看的都是最顶尖的作家,一般看两到三本,好的再看五到六本。
欧宁:你作为一个评委的阅读和作为一个作家的阅读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你是一个从来不会隐藏自己受到什么影响的人,因为你经常提起William Trevor和Alice Munro对你的影响。这两位是你在爱荷华上了那个写作课以后开始读的吗?
李翊云:William Trevor是的。
欧宁:我挺好奇你来美国之前、你成为一个作家之前的阅读,我发现你好像很喜欢沈从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他的?
李翊云:沈从文是在国内就读了。虽然我长大了学理科,但小时候也挺喜欢看书的,但小时候也没什么书,所以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我大学的时候看英语比较多,但九十年代也没有什么英语书,也就是那些经典的海明威、杰克·伦敦,我记得上大四的时候看了一些比较现当代的,比如Joyce Carol Oates、Alice Walker,那会儿在国内也都像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那样看的。


[李翊云和姐姐以及父母在北京,1978-1981年。李翊云供图]
欧宁:你在第10期A Public Space上翻译了一篇沈从文的家书,为什么要介绍沈从文?
李翊云:现在他在国内稍微好一些了,以前也是没有人看的。我看他的家书,尤其是解放后他还是在想怎么写作,但他从来没写过,我觉得是挺大的损失。可能我觉得与他在性格上比较亲近,写的东西也比较亲近,所以总是对他很感兴趣。从A Public Space刚创刊的时候我就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沈从文的家书翻译出来,后来我就跟主编Brigid Hughes说想做一期从文家书,事实上我翻的比最后那个要多得多,大概有三倍之多,但最后选了三分之一,然后沈从文的英文译者非常之高兴,给我发很长的电邮说这件事。
欧宁:大家都知道你本来是学理科的,后来到美国需要找事情来舒缓自己的压力,然后就报了写作课,我想知道,这个人生的转折难道在前面没有任何预兆吗?
李翊云:没有什么预兆,我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但是从来没想过写东西,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用英语写东西比我想的有意思。
欧宁:现在你的枕边书或者你随身带在包里的书都是什么书?
李翊云:我一般手头上会有五、六本书同时看,我在看Katherine Manthfield,她生在新西兰,然后还去了英国,她是跟伍尔芙一个时代的女作家,我在看她的日记,她一生很短,死的时候才36岁;然后有一个美国诗人,现在已经去世的Elizabeth Bishop,我在看她的信;小说我在看《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一本小说,我觉得比《简·爱》写得好但没有《简·爱》有名;还有就是当评委的这些书。
欧宁:你看中国当代作品多吗?
李翊云:不多,前几年看了一些,有时候人家请我写书评,比如英国《卫报》请我写苏童的《河岸》的书评,那样的话我会看一下英译本和原文。
欧宁:在一些采访里,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国际作家,我觉得在你的自我意识里,你在淡化自己的国族特点。的确,强调国族身份在现在看来有点落后,对于在美国写作的华裔或亚裔作家的作品,有人曾用“华美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或“亚美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这样的概念去定义,强调它的国族性,又或用“离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的概念,强调移民与母体文化的一种关系,这些说法都有点陈旧了。我觉得你用英文写作,称你为英语作家便好。我想问,会不会有一天你的小说主人公不是中国人?
李翊云:我觉得会有可能吧,未来的事情我也不能预料。我觉得有些人比如西方读者会说,他们看了一本中国书,中国妇女缠脚、包办婚姻这种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很野蛮又很新奇的概念,有人会用这种想法去读;但有些西方读者读了我的书,就会觉得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是中国人,但人性总是有共通的地方,我比较注重这些东西。
欧宁:我刚刚的问题应该再深化一下。有人说,一个作家的写作肯定离不开自己的体验,你体验过的东西或者你小时候的经历会变成你写作的资源,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超越自传,超越他(她)本身的文化和经验。有一天你会不会不写和中国有关的题材?
李翊云:那是当然的,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地有些题材不光是中国的题材了。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在越南生的,作为难民逃到澳大利亚,他叫Nam Le,可能在中国不太有名,但他在美国和英国比较成功,我们在一块上学的。逃难到澳大利亚后他做律师,后来到爱荷华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就很有意思,除了第一篇文章是关于越南的年轻人,有点类似自传,但后来的文章全是靠Research,而且每一个故事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比如在伊朗或者在纽约。他是个律师,只要做足够的准备,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材料他就会有一个Case,就能写一个故事。我觉得写书就是这样,你要知道足够多的东西,怎么飞跃一下然后变成一个成功的故事,从一些细节就能够构造出一个故事来。我觉得个人经历是帮助你理解一些东西,而不是依靠这些经历。
欧宁:我感觉你一直拒绝在你身上贴“中国”或者“华裔”的标签。
李翊云:因为我觉得贴上这些标签,会有一些作为作家来说不必要的负担。
欧宁: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记者采访时都说,李翊云用英文在美国写作,她的成功得益于美国的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也许你不会同意吧。有一次你在Facebook上说你 母亲一直问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上,你在美国这么成功,她应想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吧,但你表现出对这个问题不胜其烦。你的国族标签在世俗 层面上可能带来的问题,还包括像中国的文学出版界很想翻译出版你的作品,这里头除了市场因素,可能也有一种国族自豪感的消费需要。你一直是拒绝的,好像人 所共知,李翊云不轻易授权自己的作品译成中文,你好几次回答的理由是觉得当代中文著作已经有很多好的作品,而你是为英语读者写作的,所以没有必要翻译,这 里面还有没有更深的原因?
李翊云:有一个程度上,我觉得很多东西得重新写,不必要译。
欧宁:你是在担心自己的作品译成中文之后的竞争力吗?
李翊云:不,我觉得是对读者的相信程度。比如说我跟美国读者提到1958年,我用英文写时我得解释一句,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发生的年份,而在中国,提到1958年 所有人都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你如果把那句解释翻译回去,就好像中文读者不了解中国历史,你低估了读者的智力,我不想那样的事发生。如果说我只是写 一个人物,没有任何中国的背景或者历史背景,只是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一个人,这有可能,但我觉得所有都跟历史有关系,在历史这一部分直接翻译成中文不是很 好。
欧宁:你是否听说过哈金在台湾的故事?
李翊云:听说过,我觉得台湾人的眼界我是不敢恭维的。
欧宁:是不是哈金的事情给了你一些触动?
李翊云:我确实问过哈金。当年有中国出版商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认识,我问他怎么想,他说你做好准备再去,否则会挺难受的。可能我还想再积累一下等待一下,不是很着急。
欧宁:有很多人猜测你不想自己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原因,这些猜测跟你的回答很不一样,都猜到政治那方面去了,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李翊云: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总是在拒绝把自己叫作中国作家或者华人作家,写作在我来看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不想被别人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贴上别的标签,所以我会比较谨慎。没有什么政治原因,主要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到准备好的程度。
欧宁:我想问你对政治的看法。你一定会拒绝文学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如果不谈文学,你平时会关心时事政治吗?
李翊云:我还算比较关心吧,不能说非常关心,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要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事情在发生。我可能更关心历史,比对时事政治更关心。
欧宁:你的《漂泊者》(The Vagrants)其实就有触碰到历史、政治这样的议题,那本书的写作资源可能跟你自己的成长有一点点关系,但要写过去年代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研究的吧。
李翊云:主要是看一些老的照片、老的东西,跟普通人聊天,像我公公、婆婆,我觉得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最好不让他们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他们就跟你山南海北地聊,就会有一些很好的素材聊出来,但七十年代咱们都还是过过的,所以还是记住的。
欧宁:你平时多久回一趟中国?
李翊云:我回国倒不是很多,上一次是2008年回去的。
欧宁:不知道你现在怎样更新你对中国的认识?
李翊云:我看一些中国的网站,然后跟中国的朋友和家里人联系一下,但就像你说的最终可能会写一些不止是中国的题材,比如美国或者西方,更广泛些。像我就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可能我今天看到的是美国的东西就会写一些美国的东西。
欧宁:你有一天会否用中文写作?
李翊云:我不知道。
欧宁:呵,难道你不想参与一下中国当代文学?
李翊云:我觉得有一天也许会,怎么说呢,我觉得人就是一个阶段做一个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现阶段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可能要准备到十才会去参加这个一,更多程度上还是我觉得现阶段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由上海2666图书馆周焰根据录音整理,经欧宁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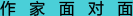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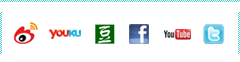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