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诗人大仙
在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千百年的否定之后,这些积累引发了关爱、欢乐以及思索、希冀、愿望、向往、沉思、胜利和无数读者,加上衣料,包起来,再覆盖——代代不停地遮盖,到那时这些诗歌才能得到承认。
瓦尔特·惠特曼——《今后许久许久》
— 圆明园迷人荒凉 —
“岁月的刀涂着口红在歌唱”——这是圆明园四才子之一黑大春将近30年前震响圆明园的诗句。1985年,我离开大山子,直奔圆明园,一帮20来岁的诗歌青年,在这片耀眼的废墟上,成立了“圆明园诗社”。

图说:1983-84年间,黑大春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朗诵。严力摄影。
圆明园当时没有一个画家,只有诗人。黑大春在福海一带借到一间农民的小屋,在这里喝酒写诗,让青春对历史咏叹,感觉特有历史感,这就成了“圆明园诗社”的象征。不过,黑大春家在中关村,我们就常在中关村活动,由于离高校比较近,我们经常去校园朗诵。那时每个诗人必须会朗诵,否则没人气。当然是背诵,绝不是念诗,我们管区别于朗诵艺术家的舞台腔调朗诵,叫做——“浪诗”。
除中关村外,“圆明园诗社”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就是六铺炕,因为诗社社长戴杰和师爷刘国越住在这里,这里几乎就成为“圆明园诗社”的大本营。一帮写诗的整天在这里喝酒碴诗,大半夜的经常去人定湖对着夜色和湖水嚎叫我们最喜欢的诗句。记得在拂晓的北京西城街区,我们酒意盎然诗兴大发,高声嚎叫着金斯堡的《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毁坏,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体,拂晓时拖着脚步穿过黑人街区寻找一针够劲的毒品……”
当时我们爱管自己叫写诗的,管画家叫画画的,管作家叫写小说的。在诗歌的奋斗年代,我们对“装”是很厌恶的。
1984年岁末,我在《北京晚报》中缝里看到一则广告,崇文区文化馆将举办诗歌讲座班,有江河、杨炼、顾城讲课。看到这三位的大名,就像现在小孩听到周杰伦什么的差不多。于是我花十块钱报了名,并在讲座班上认识了顾城和杨炼,江河因为在外地采风没来讲课。也就是在这座诗歌夜校中,我认识了诗人阿曲强巴,阿曲又把我介绍给“圆明园诗社”成员殷龙龙。从原创意义上讲,位于磁器口的崇文区文化馆开办的诗歌夜校,成为我投身现代派诗歌的发源地,当时我们上课的地方在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诗歌夜校的校长徐咏龄是我名义上的诗歌指路人。
1985年3月15日,春寒料峭夜,我穿着“纯毛舍味呢”中山装和九寸裤口的“弹力板丝呢”喇叭裤,前往鼓楼外大街拜访殷龙龙。龙龙二话没说,就把我带到“圆明园诗社”军师刘国越的家,在六铺炕刘国越的家中,我聆听了“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激情澎湃的诗歌鼓动,从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诗歌运动。后来,3·15这一天,成为“打假维权日”,我也从这一天开始,正经八百投身到热火朝天的现代派诗歌浪潮中。
此时“圆明园诗社”要在北京林学院(现已更名北京林业大学),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派诗歌朗诵会,戴杰看中了我的外联能力,让我主攻对外联络,于是我跟戴杰、刑天频繁游说北京各界的诗歌名人。
在我们努力运作下,现代派诗歌朗诵会于1985年4月5日在北京林学院强力登场,学校的礼堂坐满了校园中和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当时,正是诗歌大面积降临的年代,到处是一望无际的诗歌青纱帐。坊间有句特别喜感的名言—随便扔块儿板儿砖就能砸到一个诗人脑袋上,周围立马涌出十个诗歌爱好者救助呵护受伤的诗人。
朗诵会上,四位“今天”的杰出诗人北岛、芒克、多多、严力登台奉献佳作,袁可嘉、郑敏、吴思敬、唐晓渡、刘湛秋、杨匡满、江枫等诗坛强豪亦到场助阵,“台湾三杰”侯德健、黄植诚、谢雨辰也莅临捧场,而一度成为中国歌坛首席偶像歌手的蔡国庆也把他初出茅庐的第一歌,奉献给大江东去的“朦胧诗”。当时的“摇滚舞王”、后来成为“霹雳王子”的陶金,因有紧急演出错过了这次盛会,要不现代舞与现代诗之间,将会有一次奇特的相遇。
在这次朗诵会上,我认识了“圆明园诗社”的实力派诗人黑大春。4月5日这天,恰好是大春生日,在北京林学院光耀的舞台上,黑大春唯美而颓废,浪漫而华贵,一首凝聚古典之力的纯诗——《东方美妇人》破空而出:
啊,东方美妇人
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
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
圆明园,迷人荒凉
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在此之前,我已通过刘国越认识了“圆明园诗社”另一位重要诗人雪迪,在雪迪东直门小街中医研究院的家中,我们已碰过杯,谈过意象和通感。为了我的到来,雪迪特意去简易木板房中的小饭馆打了两暖壶散装啤酒,而我们当时的沽酒之地,如今已演变成东直门簋街的餐饮重镇——花家怡园。

图说:1983-84年间,雪迪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朗诵。严力摄影。
在圆明园的岁月中,我跟刑天处得极为沆瀣,成为诗社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黄金组合,甚至比后来姚明与麦迪的姚麦组合还默契。那时,我住大山子,刑天住西三旗,我们便把刘国越在六铺炕的家当成了诗歌家园,而温柔敦厚的刘国越,用他的和蔼善良召唤着每一位诗歌浪子,抚慰着年轻诗人被艺术折磨被理想煎熬的痛苦内心。每次,我来到刘国越的家,从藏钥匙的地方摸出钥匙,然后从橱柜里搜出方便面,煮开了就吃。诗人也得吃饭呀!那年代我们一个月十块钱足以生存,因为诗歌的力量太强大了,让我们忘掉了还有世俗生活。
1986年深秋,我和黑大春在刘国越家里喝酒闲聊。我那时已在建国门外的《北京青年报》当记者,整天在媒体与诗坛之间穿越。喝着喝着,大春乍现灵感,指着我对刘国越说:我怎么觉得丫那么像个仙儿呀!干脆叫他“大仙”算了。刘国越说:没错,你以后写诗就叫“大仙”,不许再用“微茫”,微茫太拽了,大仙多气派呀!于是,我的笔名“大仙”就这么定了。大春还跟我调侃,以后出诗选按姓氏笔画排位,你还排在艾青和北岛前头。
1988年,徐敬亚、孟浪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书中刘国越以“隐南”为笔名撰写“圆明园诗社”的概况,并首次正式提出圆明园四才子——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这一称谓。而今,我们四人早已各奔东西,难以聚首——黑大春在诗歌深处继续蛰伏,雪迪去了美利坚,刑天纵横于股票期货中,我则忙着张罗各种饭局聚会。
— 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
1985年,“今天”诗人已经如雷贯耳了,由他们引发的“朦胧诗”潮在全国迅速蔓延,大有席卷甚至吞噬保守派诗歌之势。我比较反感“朦胧诗”这一称呼,有点儿嫩俗小清新之气,与诗歌的沉雄幻美不搭,与诗人的生命形态满拧,倒跟后来琼瑶的通俗文艺小说貌似沾边儿。像我们“圆明园诗人”以及西川、海子为首的北大四才子,绝口不提“朦胧诗”,我们管“朦胧诗”叫现代派诗,称北岛他们为“今天”诗人。

图说:《今天》创刊号封面
这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惊蛰中萌动着诗歌的气息。北京这座古城,新诗潮在汹涌,整个生活都被诗歌潮流带着往前涌。此时,我正忙着写毕业论文,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大学首届中文系半工半读带薪上课的一名学员,我的论文选题是现代派诗歌评论,题目叫《北岛与杨炼》,我的指导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后来,这篇毕业论文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当代理论思潮刊物《青年论坛》上。
1985年的寒冬,在崇文区文化馆举办的诗歌讲习班上,我结识了前来讲课的杨炼。基本上每星期一到两次,我从我的住地大山子,杀向颐和园北宫门杨炼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住地,在搜集论文素材的同时,也忙里偷闲向杨炼老师请教一下诗歌。杨炼那时三十而立,留着长发,声如洪钟,语言表达极具感染力,一上来就跟我侃埃利蒂斯飞翔的超现实主义——“高飞的鸟减轻我们灵魂的负担”,我则以英国超现实主义诗歌鼻祖大卫·加斯科因的“他们上面的太阳是一袋铁钉”应对。杨炼觉着我还有一定的诗歌常识,算跟我聊得比较投机。杨炼是好酒量,我的酒量也不弱,这样我们在“诗酒趁年华”中更加投缘。

图说:诗人杨炼
在西临颐和园、东望圆明园的国际关系学院宿舍楼,在与杨炼混熟的同时,我认识了菲野,也就是荀红军,他身上有种“白俄浪子”的气质,是中国翻译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的奠基人,翻译曼德尔施塔姆(当时我们叫曼杰斯塔姆)是他的拿手好戏。当时通过杨炼介绍,我还认识了就读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文学专业的刘欢。杨炼说:这哥们以后唱歌将前途无量。果然,日后的刘欢高歌猛进,震烁歌坛,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高唱奥运主题歌。不过,当时刘欢挺服我们的,说你们写诗的把艺术搞成了纵横天下的气势。
由于我的论文涉及北岛,所以必须要见到北岛,征求他的意见。北岛在三不老胡同的地址,是周国强给我的。周国强写诗时的名字叫阿曲强巴,他在给我北岛地址时,特意叮嘱我:千万别跟振开说是我告你的地址。当时北岛在诗坛名声日隆,已有些神秘高拔的色彩。我按照阿曲强巴给我的地址,给北岛写了一封信,要求就论文一事登门拜访。为了有说服力,我把早已求得的谢冕的推荐信也一起寄去。北岛是严谨的,我不能显唐突,诗坛虽如江湖,但入道也讲规矩。很快,北岛回复了,说可以见。
在1985年初夏的午后,我来到厂桥三不老胡同北岛的家里,拜见现代派诗歌“大龙头”。由于今天同仁把北岛形容为“老木头”,我想象中的北岛冷漠、刻板、不苟言笑。及见到北岛本人,发现他挺温和,并没那么端着,谈吐也不拒人千里之外。在客厅里我见到了北岛的父亲,一位清癯文雅的民主党派人士,跟我有礼节地打了个招呼,然后退出客厅,把谈话的空间留给我们。
我们先聊了会儿谢冕,聊了会儿杨炼,还有我当时参加的“圆明园诗社”黑大春、雪迪什么的,随后我向他介绍我的论文《北岛与杨炼》的大致意图。北岛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他说:我跟杨炼的诗风并不一样。当时杨炼的《诺日朗》已经声名鹊起,一度成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本,坊间传闻杨炼可能就此被“招安”,其实杨炼的骨子眼里是很“地下”的,他的精神世界有种坚强的另类。我跟北岛解释说:主要你们是现代派诗歌不同风格的两个代表,诗风大相径庭,却又各领风骚,我也是把你俩独立成章,并不做太多的比较。北岛不置可否:行吧,写完之后,寄一份给我看看,毕竟现在写我们的论文还没有。
然后我打开我的剪贴薄,上面贴着很多“今天”诗人发表过的诗,我把两首北岛在《丑小鸭》发表的诗给他看,并说:这两首诗我比较喜欢,论文里会涉及到。一首是《雨夜》,北岛看了一下,就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中的“太阳”改成“朝霞”,并说:这是编辑的误发,或者擅自改动,“血淋淋的太阳”,意象不通,我原诗上写的是“朝霞”。随后,北岛又把另一首《雨中纪事》改了一下,“雨水冲刷的——是泥土,是草,是哀伤的声音”。他提笔将“伤”一圈,改成了“怨”。没错,哀怨的声音,比哀伤的声音,更给力!
当时我写诗的笔名还不叫“大仙”,用的是“微茫”,我把完成的论文寄给北岛时,署名就是“微茫”。后来北岛跟别人说:大仙刚出道时,名叫“微茫”。我想,北岛开始也不叫“北岛”,而叫“石默”。
1995年,我去斯德哥尔摩采访第二届女足世界杯期间,见到了万之(陈迈平)、严力和李笠,万之请客我们小聚了一下,席间万之把北岛在巴黎的电话给了我,采访完女足世界杯,我要去趟巴黎。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共电话厅,我给北岛打电话,说我特意到海外来拜见“大龙头”,北岛在电话里说:那咱们找天聚一下。我说:不麻烦了,就跟你打个招呼,我也呆不了几天。
认识今天的“诗歌王子”顾城,也是在崇文门文化馆的诗歌夜校,他跟杨炼一样来给我们讲课,后来我跟杨炼混熟了,杨炼把我介绍给顾城。1985年10月,我来到位于海淀区翠微路小学里的《中国电子报》当记者,便有了跟“童话诗人”顾城接触的机会。顾城住在万寿路总参大院,离我只有半站地,所以我经常去万寿路拜访这位诗歌天才。
12月的一天,顾城和谢烨包饺子请我吃饭。我第一次来到顾城的家,看见门上和墙上画的全是鱼,现在回想起来,比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要灵幻多了。顾城说这是他画的,画给老于的,老于于有泽就是“朦胧诗”的另一位卓越人物江河。江河将顾城视为弟,顾城把江河当成哥,当然,顾城当时还有一姐,叫舒婷。
顾城带着优雅自恋的白色厨师帽,给我讲房子、鸟儿、麦穗、湖水等一系列打动他的诗歌意象。谢烨知道我爱喝酒,特意准备了通化葡萄酒。我们吃着饺子,顾城、谢烨喝茶,我喝酒,回忆1985年夏季昌平诗歌笔会的情节。就在这次笔会上,一位“极左诗人”疯狂向顾城叫板,而刚到《诗刊》参加工作的诗歌少女李英,后来变身为麦琪和英儿,以自己23岁的青春身躯,毅然站在顾城一边,奋勇抵抗“极左潮流”对现代派诗歌的绞杀。等到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出事之后,我才猛醒,“昌平笔会”竟是“激流岛”的序曲。
不管顾城在“激流岛”如何人鬼合一,不管顾城的“利斧袭妻”事件如何触目惊心,我是一个局部唯物论者,起码在1985年稍纵即逝的日子里,在天伦之光的照耀下,顾城和谢烨是美好的、是幸福的、是明亮向上的,他们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中国男女的传统恩爱,没有任何血腥的前兆。
冬日午后的万寿路暖阳高照,顾城和谢烨一路上送我,两人相依相偎,形影不离,那种感觉,现在一想起来,绝对是至善至纯。我离顾城、谢烨远去之际,猝然回首,谢烨正眼睁睁望着顾城,抚弄着顾城的鬓发,真像林忆莲后来唱的——“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
1986年深秋,在诗歌评论家吴思敬王府井的家中,吴老师猝然感慨:顾城都30了,北岛快40了。当时我心中凛然一惊—诗歌的光阴真快,20多岁刚出来混,转眼就直奔三张。诗人是短命的天才,是青春期的流星,过了30,意味着爆发力减退,语言的造血功能削弱,抒情的才华下降,冲击灵魂核心的能量逐渐丧失。
“今天”诗人中,我第一个认识的是杨炼,混得最狠的是芒克。认识芒克,是通过黑大春介绍,当时我们都管芒克叫“老猴”。“今天”初期,赵振开与姜世伟互起笔名,赵振开称姜世伟为“芒克”,姜世伟将赵振开命名为“北岛”,于是这两个响亮的名字日后扫荡诗坛。

图说:年轻时的芒克(左)与北岛
芒克当年是跟我们“圆明园诗社”走得最近的“今天”诗人,他最早住三里河纪委大院,跟号称“啤酒主义者”的作家狗子是街坊。我认识芒克的时候,他已经搬到劲松415楼,他的一室一厅的小屋,一度成为“圆明园诗社”解体之后我们诗人的啸聚地,后来又成为“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大本营。在他家混时基本以喝酒搓麻为主,很少谈诗歌,因为芒克认为,老谈诗歌忒事儿逼,诗歌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芒克是诗歌天才,他寥寥读过几首外国大诗人的作品后,直奔诗歌高峰而去。
1986年12月31日,我们在芒克家迎接新年,六个哥们热血一涌,拜了把子。当时我们已从“地下”诗歌跃到“地上”,诗坛一片混战,互相攻击,争抢地盘。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而又僧多粥少,所以诗人之间,党同伐异,掐起来没完。抱团是必须的。我们把子一拜,貌似“劲松六结义”。老大:芒克,生于1950年;老二:雪迪,生于1957年;老三:刘国越,生于1958年;老四:大仙,生于1959年;老五:黑大春,生于1960年;老六:吕德安,生于1960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喝狂聚了大约一礼拜,然后各自回家,闷头写诗。
第一次见郭路生(食指),我们都管他叫老郭,是在“圆明园诗社”分崩离析之后,1986年的12月,是在黑大春中关村的家里。那是一个西方文艺思潮无比泛滥的年代,当时,北大正加紧筹备“北大艺术节”,北大“五四文学社”邀请“今天”、“圆明园”、“北大帮”以及其他现代派诗人,于12月26日这天在阶梯教室登台朗诵,取名“北大艺术节”现代诗歌朗诵会。食指和芒克是重头,当时食指正在遥远的昌平县沙河镇的北京第三福利医院饱受病魔的煎熬。一天,黑大春突然把食指接到自己家里,我们正在讨论艺术节朗诵会的流程,食指的到来让我们格外振奋。老郭虽然有些病态,但精神很顽强,思路也清楚,跟我们聊得很开心。他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是朗诵会必“浪”的极品。考虑到食指的身体状况,大家决定他不上场,而由一位师大“北国剧社”的女大学生郭晴丽代他朗诵。朗诵会那晚,郭晴丽在配乐中声情并茂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在“浪”到“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时,郭晴丽特意把手指向老郭,看得食指一阵激动。
老于,于有泽,就是江河,是我最后认识的“今天”诗人,我们只见过两面。他住在阜成门宫门口期间,挨着阿曲强巴,我经常去阿曲家,却无缘造访江河。及至蝌蚪自杀之后,1987年春我来到江河迁至通县的家(当时还不叫通州),在那住了一宿。我们喝酒,谈生命,江河的家里全是西方高雅音乐唱片,他给我放瓦格纳和勋伯格,我听不懂,假装沉浸在勋伯格《升华之夜》的升华中。
“今天”怪杰多多,真名粟世征,我们爱叫他“毛头”。他比较恃才傲物,属于诗歌狂人,不好接近。他家住什么地方我真不知道,只知道他在朝阳路十里堡的《农民日报》上班,当时我在《中国电子报》上班,算是同行。每次见多多都是在别人家里,有回在芒克家,喝酒正喝美了,多多起身就走。我问他着什么急撤?再喝点儿。他背起双肩包说:哥们是班儿爷,明儿早起还得上班,喝大了骑不了自行车回家。还有一回在雪迪家,我们聆听多多的教诲,他说诗歌要“短而锐”,要反着写,比如——“从死亡的方向往回走”。然后他用美声唱法般的唱功给我们念几位作家诗人的名字:骇——明威、普辣——斯、艾滋拉——乓!
严力当时住上海,偶尔来北京云游,我们见得不多。不过上世纪末,我在三里屯豹豪酒吧严重晃点过严力一次,约好了晚上一起喝酒聊天,但我前一晚通宵大酒整残了,就爽了约,至今还想当面向他道歉。“今天”还有一位隐秘的诗才,就是田晓青,他是圣琼-佩斯的狂热爱好者,我也喜欢佩斯,我们正好聊到一块儿。田晓青住南礼士路,我们约在真武庙的新疆小馆喝酒,他说有一回碰着杨炼,印堂发亮,话语铿锵,跟他说——刘索拉、徐星都火了,你还不写两篇恶小说,出出名!
— 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 —
为秋天而存在为你心中的四季而聆听
八月之琴在芦苇的手中奏响
众鸟的天空有一轮落日倾向大海
黄昏,在石头的双颊上涂满浆果
1988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诗歌板块,以我这首《再度辉煌》打头,那一年我29岁,直奔三张,正处于写诗不要命、为艺术而艺术的激烈阶段。后来我去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文联大厦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拜访主管诗歌的韩作荣老师,正好遇上当时的主编刘心武,心武鼓励了我一句——年轻的诗人,好好写,写出更漂亮的诗歌来。
1988年,在那个诗歌飘香的年代,我心中充满诗歌理想,在中国的诗歌土地上勤奋耕耘。那个艺术与灵魂的年代,诗歌的魅力已迸发到顶峰,诗人的位置至高无上。随便扔一块板儿砖,就能砸到一写诗的脑袋上!20后、30后、40后、50后、60后的大群诗人集结在一起,在1988年、1989年这两年中,谱写出中国诗坛最后的狂欢。
我的诗歌黄金生涯比较短暂,跟青春期的冲击力有关,1989年之后,青春好像就没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是一种艺术手淫和语言做爱,灵感与才情需要荷尔蒙与内分泌的大量充填,光充填还不行,还得释放与爆发。诗人是一个出色的手淫专家,也是一个冲击异性的角斗士,当然这一切都得像兰波或魏尔伦那样,最终宏大地返回语言的核心。
我从1985年进入“圆明园诗社”之后,便与现代派诗歌打成一片,先锋诗歌绝对摒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年代,我们写的诗要是让读者立马看懂了,形同于侮辱我们的智商,等同于糟蹋我们的灵气,我们在“地下”诗坛就没法混了,顶多算一诗歌爱好者。
1987年刚过完五一,芒克把我叫到他劲松的家里,兴致盎然地说:要有大行动,我们要成立诗人俱乐部,你们圆明园的将成为第一批成员。我听了很激动,“今天”终于跟我们联手了,虽然我们处于从属地位,那也很牛逼呀!芒克所说的我们,就是他和杨炼、唐晓渡。那时,杨炼、唐晓渡相继搬到劲松,三人一拍即合,组成中国诗坛的“劲松铁三角”。芒克住劲松415,杨炼住414,唐晓渡住316,从人文地理来说,真是绝佳组合,胜过一度极为强势的“劲松三刘”—刘再复、刘心武、刘湛秋。
1988年夏,我接到“劲松三杰”芒克、杨炼、唐晓渡关于成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邀请函,便从大山子欣然奔赴劲松去找组织。“幸存者”的宗旨我现在还记得——
“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幸存”的必要和可能与精神的死亡本于同一渊源。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幸存”意味着把握住那些最致命的一瞬,在其中安顿下来,并将其作为造物的启示交还给人类精神。
“幸存者”是孤独的,或者说是独立不依的。他既不是众神的后裔也不是历史的人质,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在这个充满喧嚣和骚动的世界上,他更愿意经常处于沉默无名的状态。他就隐身其中与死亡对弈。从而把苦难转化成自由,把宿命转化成使命,把羞辱转化成高贵,把贫困转化成富足,把创造和幸存作为同一的精神盛典加以享受。
“幸存者”对诗和艺术的选择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是至高的选择。但真正的、唯一的“幸存者”只能是诗和艺术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幸存”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奉献。这就是我们如此偶然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如此必然地在这里聚会和歌唱的原因。

图说:《幸存者》第一期封面及目录
一望而知,这便是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才子唐晓渡的文笔,他的这句“‘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引导着我直杀进90年代社会大转型后的物质社会,却依然好使。那时候的文学女青年一听说你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就特别激动,要求我也帮着她们“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诗歌形而上的本质,这时候就显出高贵来了,正像罗伯特.勃莱说的:“现在它必须在死亡之外会见死亡”。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成立“大趴”,于1988年7月在西便门的三味书屋豪情上演,与会嘉宾有当时刚演完《红高粱》的未来中国影帝姜文,不过,当时我们写诗的还稳坐中国文化的第一把交椅,所以没什么人理姜文。记得1986年秋,我参加“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王克平在建国门外交公寓召集的“趴踢”,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第一美女林芳兵也来了,正缠着北岛切磋诗艺。北岛看见我,赶紧把我叫过去,跟林芳兵说:大仙也写诗,你跟他多聊聊。我接过林芳兵就说:从哪儿聊,是从舒婷的《致橡树》还是顾城的《一代人》开始聊?林芳兵把她发表在《大众电影》上的毕业礼赞背诵给我听,我说:还不错,就是意象上差了那么一点儿。林芳兵问我:什么叫意象?我说:就是意境中的表象。林芳兵说:这可太深了。我说:别管它深不深,咱先干杯酒。

图说:“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部分成员
关于江湖上流传“幸存者”讨伐海子诗歌一事,甚至夸张延伸到海子最后自杀与此次讨伐有关,作为当年现场的目击者,我认为言重了,那不是讨伐,而是切磋,虽然多多当时的话有些愣,可能切磋得有些严厉。“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后,一般每个周日都要开一个诗人的作品讨论会,交流促进诗歌写作。开会的地点实行轮换制,先在“幸存者三巨头”芒克、杨炼、唐晓渡劲松的家里搞,而后在东直门小街雪迪家、团结湖的一平家搞过,海子作品的讨论是在王家新和平门的家中。那是1988年12月的寒冬,海子先朗读他的长诗《太阳·七步书》中的《太阳之弥赛亚》,诗篇很长,我看出多多有些不耐烦。终于等到海子读完诗,多多抢先发言,他一向快人快语:能不把诗写这么长么?海子一愣:我这是长诗。多多说:最好不写长诗,对语言来说,短诗就够了。海子比较执拗:可我觉得不够。这期间还有插话的,场面争执得比较混乱,之后,多多男高音的嗓门中确实喷出一句——反正你这么写不灵。至于他对海子说没说过“你不适合写长诗”,确实记不清了。这样的争执、所谓的艺术冲撞在我们当年的奋勇碴诗中屡见不鲜,大家没有任何恶意,只是讨论作品,不触及人身。我想,以海子对诗歌的透悟,不至于对这场争辩想不开吧?况且,他的短诗就是比长诗强。
进入1989年,“幸存者”开始筹备一次大型的诗歌朗诵会,经常在芒克的家里举行筹备会,芒克住的那幢楼——劲松415,俨然已成“幸存者”的地标。北岛、食指也来了,还有顶替已出国不能登场的杨炼朗诵的学者刘东。北岛突然显得幽默,跟刘东说:你哪儿像杨炼呀?太不像杨炼了,干脆你弄个杨炼的面具戴上,然后高吼一声——高原如猛虎!绝对震了。食指那时精神已经好多了,芒克问他:你上台没问题吧?能顶下来吗?食指精神矍铄地说:我行,绝对行。
春天到了,离“幸存者”朗诵会的日子越来越近,在现在文艺小清新最爱盘踞的南锣鼓巷东棉花胡同的中戏小剧场,“幸存者”组织了一次彩排。我和张弛因喝酒迟到了,遭到了“幸存者领袖”芒克的训斥: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赶紧上台彩排?下次再迟到,取消朗诵资格。训得我们心里直犯嘀咕:这也讲组织纪律呀?通过这次彩排,我得知给我们这次“幸存者”诗歌艺术节当总导演的,是任鸣,现为人艺副院长。
1989年4月2日,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在中戏小剧场成功举行,1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还有1000人站着直到终场。这绝对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次盛典,造成周边交通二级预警。

图说:“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的纪念册封面及“献词”,唐晓渡执笔。
我至今依稀记得“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那些诗人们:食指、北岛、芒克、多多、杨炼、唐晓渡、王家新、林莽、一平、西川、海子、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张弛、维维、镂克、莫非、童蔚、张真。
1989年的岁末,格外寒冷,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90年代,即将在晨曦中跃出,诗歌的黄金岁月——80年代辉煌的吟唱行将结束。诗歌带着使命、也带着心碎无声地滑向世纪末,一个貌似繁华、实为浮躁的功利社会就要无情地席卷而来,排山倒海的商业大潮很快会淹没诗歌忧伤的韵脚。
我在一夜大酒中过完30岁生日,看到地毯上横七竖八躺满在醉梦中流连的诗歌男女青年,残酒在脑海中击荡,喉咙中是劣质烟草的堵塞和酒醒之后的干渴苦涩。走进岁末的寒流中,太阳冰冷得像一具僵尸,很多诗人已离开祖国奔向欧美,而那些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着紫禁城飞奔。在80年代最后一抹残阳中,诗歌正在向我们的灵魂告别,诗人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种族,诗歌优雅的呻吟已封存在高贵的心灵中。在未来,在20年之后,诗歌就是物质社会最后一口氧气,一如狄兰·托马斯的旷世吟唱——
我唯一高贵的心灵在所有爱的土地上
都有见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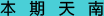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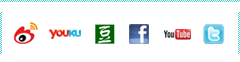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