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南》:你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又要努力成为“一个写作的皇帝”,你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写作究竟反抗了什么,才成为一名“叛徒”;而一个作家,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称为“写作的皇帝”。
阎连科:我们经常会把“写作的叛徒”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与我们特定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写作的叛徒”一定包含对这些的背叛和批判,但更多地是要包括,不仅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去写。这种背叛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对读者、对批评家的一种挑战,我们可以完不成它,但我们不能去顺从它。其实,做为一个“叛徒”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相当高相当高的荣誉,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而言,“叛徒”这个词毫无疑问是个贬义词,但对于写作,这是相当高的一种荣誉和褒扬。我在努力去做,并不一定能做到。
为什么要作为写作的皇帝,说白了,就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中国皇帝,是能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那我想作家面对稿子,要像皇帝一样,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要达到那样一种天马行空、来去自如的程度,这说起来容易,但要达到可能要费很多周折。
对于写作而言,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无法背叛自己。你可以背叛所有的写作,可以背叛今天所有的社会现实,用另外一种眼光,或者说用现实敌人的眼光去看待现实,而不是用现实朋友的眼光去看待,这都能做到,但问题是背叛自己是最容易也是困难的事情。背叛自己之前的写作,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大作家而言,都是最难以做到的事情,你可以背叛民族、背叛国家、背叛社会现实,背叛历史,这都有可能做到,但你要背叛自己之前的写作,这是最难的事情。
《天南》:你最新的作品《四书》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触及这样的体裁,你在创作之初就应该能预知到这样的结果,是作家的勇气、使命感,还是野心促使你想写这样一部作品?你怎样看待一个作家的勇气?
阎连科:从写作上而言,并不是有勇气的作家就是好作家,有勇气就能写出好作品。我写作三十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前面有很多坎坷的经历,这些坎坷的经历会对我的创作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我一再说,因为《为人民服务》,我并没有把《丁庄梦》写到最好,《丁庄梦》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我做了很大的妥协与让步。以我的年龄、我的经历,我自己的写作环境,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写出一部有相当冲击力,艺术上有相当探索的作品,一定要放弃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要放弃出版的机会。这次写作,真的不是为了出版,真的不是为了今天现有读者的口味,我仅仅是为了某一种表达。为了考验自己写作的想象力,为了考验自己写作的探索精神,我已充分做好了不出版的准备,这不在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内。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更能充分张扬、表达自己的想象力,更能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所以就有了《四书》的写作。
《天南》:中国很多作家都在“现实主义”传统中丧失了想象力,而你又是特别推崇想象力的作家,但同时你又格外关注现实,你甚至提出了“神实主义”这样的概念,我想知道你在创作时,是怎样整合想象与现实距离的?
阎连科:我在《发现小说》这部小书中,非常清楚地提出一个观点:现实主义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我们从来没有弄清过什么是现实主义,每一个中国作家、每一个批评家、每一个读者都在谈现实主义。不论什么样的小说,都把现实主义这个帽子戴在头上,但是什么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从来没有仔细分析过。
其实,现实主义最大的核心就是真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作家都会说自己的写作是最真实的。卡夫卡,我们说它是极其真实的;马尔克斯,我们也说它是极其真实的,但真实一定是分有层次的。我在《发现小说》中将真实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控构真实”,所谓“控构真实”就是被权力控制虚构出的真实;第二层是“世俗真实”,以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为例;第三层是“生命真实”,以鲁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例。第四层是“灵魂真实”,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例。我们今天的小说,其实都属于第一层、第二层现实主义层面上的真实,我们并没有达到“生命真实”的高度,更没有达到“灵魂真实”的高度。
既然现实主义在中国走不通,那我们能不能用“神实主义”呢?我认为,“神实主义”既是中国的,又是有别于西方的;既汲取西方的写作经验,同时又是非常东方主义的。“神实主义”最大的核心,比如小说的因果关系,故事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外因果,而是内因果。这种因果关系不在生活的表面、不在生活的逻辑、不在故事的逻辑,而是在故事的核心、故事的灵魂中,完全是在生活的内部发生。
阎连科:我非常喜欢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他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首次把阴界和阳界打通,阴界和阳界的人彼此是一样的、无法分辨的。我们虽然有聊斋,有很多神话故事,作为读者能很清晰地知道,这个是人、这个是鬼、这个是神,它是有界限的,但在胡安·鲁尔福的笔下,这些是没有界限的,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我来说,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尤其在民间的一点点经历是我很大的写作资源,民间有一种自成体系的真实。民间的真实性,却是我们今天所放弃的东西,我们今天讨论的真实,一定有社会真实和民间真实的区别。比如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不是民间真实,虽然也是真实,但那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真实。但在我家乡的村庄,我家乡的某棵树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的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民间的真实。对我来说,我可能把民间真实和社会真实共同融进了我的小说中。民间真实对我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帮助我完成了“神实主义”的某些东西,帮我完成了我作品中荒诞性的东西。在我们对作家的创作追根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天安门广场发生事情的真实性是个伟大的写作资源,但对于一个来自于乡村的孩子,那个村头、那块坟地、那块田野上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别人却是无法感悟的,那种真实可能更极具文学的真实性。外真实,这是人人都能看到或感受到的一种真实,但我们生活中有另外一种真实,就是个别人能看到、个别人能感受到,只有些某些作家才能把它传递出来。
《天南》: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荒诞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产生传世的经典作品,但新时期文学以来,不要说能够传世的经典作品,相当优秀的作品并不多,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文学现实?
阎连科: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说,哪一部作品可以传世,哪一部作品不可以传世,这样说为时过早,它需要时间来证明。如果所有人都对今天文学不满意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说三十年代,那是个文学的时代;我们说八十年代,那也是个文学的时代,而今天,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今天,即便产生了红楼梦,也不具备那样一个传世的社会环境、阅读环境或者文化环境;今天,即便产生了托尔斯泰,他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作家。另外一点,文学经典传世之作,不仅需要作家去写,也是需要读者去养大的。我们说鲁迅那么伟大,是因为鲁迅不断地被研究者和读者所养起来的,今天我们没有这样养育经典作品的读者群,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差,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过去的文学时代好。如果我们今天是过去的文学时代,一定是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学并不比别的民族或地区的文学好多少或者差多少。总体来说,中国还是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这些作家放在世界范围内,不管他在世界上有没有多大影响,作品翻译没翻译,我认为,他并不比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作家好多少或者差多少。今天不是一个文学时代,今天确实是一个金钱时代,是一个欲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但我想,这并不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
《天南》:你不同阶段的作品会呈现出“分裂”的状态:一是对现实的介入与反映,如《丁庄梦》这样的作品;一是虚构与想象的狂欢,如《风雅颂》、《四书》这样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种状态?
阎连科:在我的写作中,我认为《四书》的现实意义比《丁庄梦》的现实意义一点儿都不差。很多年轻的读者可能对中国那一段的历史不熟悉,因为不熟悉那一段历史,就会觉得作品的想象力非常强,但他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一段历史其实是中国社会真实发生过的。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人都会觉得中国的现实太荒诞了,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那是发生过的事情,是绝对的真实。
《丁庄梦》的真实,确实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真实,但《丁庄梦》中非常想象的东西却被忽视掉了。《丁庄梦》中有四、五十个梦,被读者和批评家忽略了。这部作品,由于特殊的原因,大家无法认真地研究它。我个人觉得,四、五十个真的梦或者白日梦,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想这两部作品是有联系的,并不是分裂的。今天看,《丁庄梦》在想象力上,我可以更加强一点,因为这种想象力的加强,也会让现实的冲击力更大。我所有的想象都不会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想象力越丰富,恰恰对现实的冲击力越大。想象力越高远,他的现实性就越强,这是我会掌握的一个平衡点。我不会让想象脱离现实,彻底地飘起来、飞起来。我追求的是,愈是想象的,愈是具有现实性;愈是具有现实性,可能愈具有想象性。
《天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你的每一部新作都有对语言的探索与实验,从《受活》到新作《四书》之间,你认为自己在语言上的探索有哪些?
就我的作品而言,《受活》是极具方言性的,用这种方言去叙述它,不只是完成某种真实性。就故事来说,它大大超过同代小说,故事的传奇、故事的荒诞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所不多的,恰恰用这种方言表述它是最为恰当的。那我想这中间的微妙、奥妙,读者可以去领会它。《坚硬如水》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里面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荒诞的情节,吸引我的是《坚硬如水》的语言,我说它是红色语言。有人说它是革命语言,不管是什么语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革命将士豪情壮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些语言杂糅到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新的小说语言产生了。它和我之前,和同代作家的语言方式都不同,这种语言恰恰叙述了一个文革的故事,来对文革进行某种揭示和重新审视的时候,是恰到好处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坚硬如水》,甚至在海外,有很多人说确实没有想到小说语言还可以这样。但是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这并不陌生,这都是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我们说过的。
我想《丁庄梦》的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中国化、传统化,而我在《风雅颂》中试图寻找一种、尝试一种纯粹的知识分子语言方式。《四书》这部小说,我为什么会用《圣经》体的语言去表达它,那是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寓言性,甚至这个故事本身和《圣经》太有联系,因为小说中的故事特别像《圣经》中的一些叙述,因为相像,语言才能完成这样一个没有来由的故事。我想它的合理性就在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要面对的问题是,你下一部小说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呢?
《天南》:你这些年的创作,愈来愈倾向于象征与荒诞,用寓言来反映现实。 在具体创作中,你认为你达到了你所追求的表达吗?
阎连科:在谈到我的小说,评论界常常会认为有很强的寓言性,甚至会说阎连科是中国的寓言大师,但对我来说它是相当真实的,我永远不会放弃小说的疼痛感,我不希望你从我的小说中读到一种快乐来,我并不希望读者在我的小说中读到轻松愉快,因为我写不来,我更欣赏小说的疼痛感。所以我想在别人看来,有很强象征或者寓言、传说或神话意义的东西,对作家本人来说,它都是最大的真实。作家永远达不到他所想象的高度,你能想到一百分,但你只能达到七十分,你传递给读者的可能就只有六十分,一定是有差距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你能想到的是六十分,你可能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百分,比如说《佩德罗·巴拉莫》、《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很难有这样一种情况,你想到的是一百分,你传递出去的也是一百分。你想到的是一百分,你传递出去的是七十分,那已经非常了不得了。但确实有另外一种神性的写作,灵光照耀的写作,你想到的是五十分、六十分、七十分,你给读者传递出去的超出这个界限。很少有你想到多少就能传递多少,这是非常难非常难的。
《天南》:当下非虚构作品很流行,也能赢得很多读者的关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与非虚构作品相比,你认为,小说介入现实的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阎连科:非虚构作品中,我认为《中国在梁庄》就写得很好。其实,非虚构作品在国外早就流行过。在八十年代,我们的报告文学也曾经非常有市场,非虚构作品其实也可以视为报告文学的另一种写作。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新闻媒体、报告文学在今天不够发达,比较萎缩而造成非虚构作品的流行。人们永远渴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最真实、最现实、最社会的东西。
非虚构只是文学的一种,文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虚构的、有非虚构的,二者无法替代。非虚构必须要依托生活的某种现实,这一定是发生过的现实,如果不是发生过的现实,它就不是非虚构,但小说就可以不依据发生过的现实。对有的读者来说,读非虚构作品可能更过瘾一点儿;对有的读者来说,读虚构作品可能更过瘾一点儿,这没什么可比较的。
《天南》:你有信仰吗?如果有,我想请你谈谈信仰和写作的关系?如果没有,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与成长环境有关吗?
阎连科:如果信仰是特指宗教方面的,我是没有的。我对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没有什么特别深的研究。但有一点,如果可以把文学纳入信仰一部分的话,那经过多年写作,文学可能真的走到我生命中来,真的成为我信仰的一部分了。我写作到了今天,如果多少天没有进行创作,我说的创作绝对不是简单的两千字或一万字的写作,而是没有完成我自己认为非常独立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字,那我会觉得这几天,确实缺少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我坐在这儿写了多少字,而是这些字里面究竟有多少创造性,这对我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认为宗教一定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传统的延续。它一定是久远的历史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不仅是父亲、母亲、孩子的传承,一个村庄的传承、一个教堂的传承。他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我们是没有这种传承的,但我想,没有宗教信仰也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同样可以表达没有宗教信仰给人带来的不安。在《四书》这部书中,我是特别探索了因为没有宗教而给人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因为宗教的不存在,导致了非宗教、非人性的那种对人的毁害。我想,我并不会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思考宗教。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焦虑、这么没有安全感、这么没有归宿感,那一定是与宗教有某种联系的,那我们为什么写不出这种不安、这种焦虑,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宗教上去考虑它。
《天南》: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称为经典作品,你平常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样的?你想推荐《天南》的读者阅读什么样的经典作品?
阎连科:经典一定是有标准的,在我看来,所有经典的作品,都会对人有极大的关怀和爱。另外一点,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是极具作家写作个性的作品。对人的关怀和最独到的个人表达,这可能是经典作品不可忽视的两点吧。我们这一代的阅读与年轻一代的阅读是有差别的。比如我们会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我们也谈卡夫卡、马尔克斯等等,但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一定谈。每一个作家都有一种对经典的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八十年代的孩子会把《挪威的森林》当成经典,这无可厚非。经典毕竟是经典,但不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发现经典,我们没有能力去发现经典。在浩瀚如烟的世界文学作品中,我们没这个权威也没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去发现经典,但我们却有能力去重读经典。
《天南》:现在是信息时代,我看你也开了微博,你喜欢这样不断刷屏、iPhone、Google所构成的信息时代生活方式吗,还是更怀念农耕时代?
阎连科:我是那种顺其自然的人,属于相对比较保守,甚至比较固执的人。现在,我还是传统的用笔写作,但我并不排斥电脑带来的许多方便,今天毕竟是信息时代,你不能排斥它。
以我的年龄和阅历,还是非常想过一种既不跟这个社会割断,但又与社会现实有一段距离的生活。让我与社会现实割断,我受不了,信息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知道这个社会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我同时又非常希望和它保持一段距离。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有一种田园的向往,至少说,每一个有一定年龄的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种安静的田园生活,我们能不能实现不管它,但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梦想。
2011年7月14日,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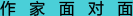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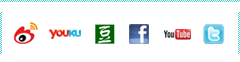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