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过许多地方,用你自己的故事记认了好些城乡以后,你终于抵达此城。
你用“抵达”这个词而不用“找到了”,这是正确的。尽管你为它走了这许多的路,但这不是一个可以被寻找的地方,它不存在。或者说它仅仅存在于世界的不可能之处,它是虚构的,只能是一个抵达的地方。
但你或许不容易看出来它的虚构。城里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都有真凭实据,每一个景物的构造都有充分的奠基。你很难说出来这城里有什么是仿造的,它也不是真实世界的倒影,这里的每一样对象都有它该有的温度和质感,甚至也能有它该有的历史渊源与爱恨情仇。你也说不出来这城里住的人是不是在城外的世界里也会有相对存在的另一个,毕竟这不能算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所在。你只能说,它是这世上某个女人(她很可能是一个文字癖)的纯粹想象,也是她这一生最复杂的创作与总结。
因为是她的城,此城已经被无数故事标签过了。你自然是该识得这些标签的,你读过她写的七本小说了。那七本书你翻来覆去地翻了再翻,觉得自己已经像读透了一本地图集似的,几乎已记下了城中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处拐角,每一根电线杆;哪里有旧楼,哪里有新房,哪里又有回教堂。啊还有你知道该到哪里去读它的历史,历史一半摊开在光处一半写在晃动的阴影中。女人总是那样处理历史的──把许多书册像晒衣服似的晾在各处,或者把书页撕下来铺贴在街上,生硬地想要把它转化成所有故事的背景。
但你不是因为这些才认出了此城。首先,你不能不认得那些雨,雨在所有的特征之上,它们没完没了,仿佛下了一世纪。久雨让一整个城市看起来病恹恹的,像小说里写的一样。那女人写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雨,每个字都湿嗒嗒,故事潮了也没有发霉的机会,下一场雨马上又来了,下一个故事随即像街灯似的点亮场景。人物们一个一个打着雨伞,有的披着雨衣,从这个故事穿行到那个故事,然后开着亮起雾灯的车子,用雨刷拨开雨水,堵在车龙里慢慢慢慢绕行,又回到这个似曾相识的故事里。
你也认得雨中的其它景物,街灯有如一根一根点燃了的香烟;有扑棱翅膀缓缓上升中的一只两只灰鸽子,有窗,有从窗洞里伸出来要带上窗门的手,有窗台上歪着脖子整理羽翼的麻雀或乌鸦或喜鹊,有墙上晾着的衣衫干了以后依然湿漉漉的影子,有窗里冷然观察着世界的猫,有鼻里喷着热息的孩子双掌贴在窗玻璃上静静注视楼下的街景。这些都太熟悉了,你在那女人的小说里一遍一遍地温习过与之相似的景致,你甚至马上觉得自己在这熙来攘往但人们木着脸不言不语的街上闻到了那女人的热带气息。
关于那女人的火热,你读过的小说里有一篇《张望的人影》可以考据。
(……温热的汗珠缀在她背上,在胸脯,在腋下,在大腿内侧。这肉身似花如玉,密缀雨露。其时他俩初见,这女人没一点羞涩,毫不扭捏,在床上是一株盛开的荼靡。张望后来一直记不起来,从机场到酒店,那路他们是怎样走的。似乎谁也没牵着谁的手,似乎女人一直在前面领路,三两步之遥,不时拧过头来对他微笑。
他是想要捉住她的手的,这情景他之前已假想过千百遍了,早在他们约好了见面的日子直至他半寐半醒地在飞机上坐了半天,这想象都不曾消停。张望原以为他们会在相见的一刻便禁不住在机场大厅里相拥,甚至热吻,为此他还特意在飞机着陆前先在窄小的盥洗室里刷了牙,用带来的面巾擦了把脸。然而那机场的接客大厅比他预想的宽阔,却又出乎意料的冷寂。有几个衣着笔挺的人手举各种姓名牌,取暖似地挤在一块,女人就站在他们身后。他们一眼认出了彼此,可在目光相接的一瞬,女人忽然腼腆地别过脸,目光停在大理石地面映照的人影上,似是懊悔了不愿意相认。
到了酒店房里,她像是换了个人,或许是终于舒了一口气,仿佛之前一直顾虑着背后会有人跟踪。门才关上她便吻他,双臂环上他的脖颈,交缠如蛇,张望慌张地应对着那吻,脑中想起年轻时在乡下写生碰见过的印度蛇神那伽的画像。那吻很激烈,女人的唇舌比他的贪婪,很快让他感到窒息;房间在旋转。要不是身上穿着衣物,女人或许就会把身体嵌入他的胸腔,将自己供奉在他两肋之间。──《张望的人影》)
记得在她的另一篇小说里,某个清冷的女子转过身去,用薄薄的背影幽幽地说,人们总是在问,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是雨季?
雨季就在这时候,在任何时候,也因此这城早已没有了雨季。这样的城符合你对那女人的小说的一切想象。在这里,唯一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你的父亲。你知道他每一年总会到这儿来待几天,像小说里的张望那样,每一年,当你们住的地方正值旱季,母亲为了如何维持家人的用水以及保住庭园里的植物而抓狂,父亲会找各种理由自己出一趟远门,途中总会转到这里来,住进女人的小说里,有时候在旅馆,有时候在有两个窗台的小楼上,以不同的身份和名字,与女人度过几日的厮磨。即使在他人生晚期(母亲说他那几年在房事上已力不从心),只要还能行动,他也坚持着这年年有今日的约会,到这里来,到小说里。
●
你所知道的父亲是个木讷寡言的人,其貌不扬,瘦得像影子。他年轻时学画不成,在美术学院辍了学,之后便学精算与计算机,一辈子勤俭谨慎,也跟着风潮搞了各种小投资,怎么说这一生虽不至于蝇营狗苟,但绝对实实在在,没有半点浪漫色彩。而母亲本来就粗枝大叶,不善于观察,从来不曾担心丈夫这样的人会在外面胡来,因此一直疏于防范,甚至连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随身带着那个“喜”字钥匙扣,她也说不上来,更别说因此生疑了。
事实上,要不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你读了他留下的那七本小说,或许你自己也永远不会觉得那钥匙扣有可疑之处。但父亲故后,你对他的所有怀疑,终是在读到那一篇区区千字的小说以后才算获得了最有力的“证据”。小说里写的钥匙扣,父亲也有一个,不折不扣,就是个被拆散后孤单的“喜”字。
(……有那么两三分钟,她和丈夫,还有那拿着“喜”字钥匙扣的女人,就那样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有几只鸽子飞来,落到三人的脚下。她把身体往丈夫靠拢一些,也特别温柔地把带来的饲料倒了一些在丈夫的手心。男人很高兴,显然,随着他的病情加重,终于把家人全都忘记以后,到公园喂鸽子成了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
男人给每一只鸽子取名,跟它们聊天,把它们当老朋友般对待。可他记不住人们的脸。有时候早上醒来,他会以一种充满疑惑和戒备的眼神,像打量陌生人似的瞪着她看。尽管如此,他偶尔还会掏出钥匙来把玩,并且对着那钥匙扣怔忡良久。
一个半圆形的“喜”字。银灰色,某种合金材质。
那是许多年前,男人调到外地去工作两年后,带回来的一件随身之物。她看出来那“喜”字里藏了磁铁,可以猜想它本来与另一个对称的半圆形相连。是半个“囍”字啊。她忍住不问,但暗中观察了好些日子,发觉男人的行踪和银行户口都没有异样,也就决定不去提起了。
十多年来,他们搬了三次家。可无论搬到哪里,换了多少次门锁,丈夫用的都是同一个钥匙扣。一个不圆满的“囍”,一个孤单的“喜”。它夹在其它钥匙之间,看来也像一根钥匙,能开启一所她不知道的暗室。──《钥匙扣》)
写小说的女人显然太高估你的母亲,把她想象得过于婉约大方。但这篇小说所表露的善良让你对作者油然生出好感,也许因为这样你才会耐着性子把七本小说全部读完。你试图在小说里寻找你所不知道的父亲,但女人写作的手法十分隐晦,许多欲言又止与顾左右而言他,因此不管你读了多少遍又怎么努力拼凑,结果总是不完整的。父亲是不完整的,女人是不完整的,时间、欲望和爱也都不完整。
以后好些年,你总是时而想象着有一天与这写小说的女人相遇。有时候你夜里失眠,会忍不住把那些小说找出来重读。你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想象她了,甚至未发觉自己已经在想象中演出了自己的父亲,通过文字进入了她的身体,与她一遍一遍地交欢。
这是你这些年的梦,不为人知,有一种乱伦般的可耻性质。却也因为这梦的可耻,它的罪性,让你愈来愈沉溺。你年轻的妻子是个细腻敏感的女人,但也不曾发现你的怪癖。至于那七本书,因她不懂得中文,除了听你提起而略知你的父亲可能有过的艳史以外,她完全不察觉你已经一次一次在出发的路上,一次一次想着要遇上那一个抵达的城市。
●
你在这个终日下着雨的小说世界里流连了几日,慢慢发现了这城市的特性。这城里的热闹繁华只是一种假象,它的实际人口并没有你所见的那么多──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分饰。那女人喜欢把她所知道的每一个人,包括她自己,以特殊的方式分解后融入想象和文字里进行复制与创造,就像拿一根肋骨创造出一个夏娃。
或者说,你悲伤地发现,这城中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了。(显然这不是你的句子,这是在一篇叫《短歌》的小说里,女主人翁春离对她的情人说过的话。)
那是七本书里你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尽管看他拖着那样硕大笨重的一个行李箱,背上还有个龟壳般巨大的背囊,他那么瘦,步履都有点蹒跚了,春离却没有上前帮忙,只是抱着手站在门口怔怔地目送。他在等电梯的时候随口说了些叮嘱的话,什么天气凉啦你这热带鱼得好好照顾自己,做家事的时候切记小心,别又拧了脚撞伤了头什么的。
“一个人在这里,多凄凉。”
春离没应声,只一个劲儿点头。那时真入秋了,白天有摄氏20度吧,春离身上已经披着她唯一的一件毛衣。那毛衣鸭绿色,很宽松,袖子特别长,春离喜欢抱着手,把手交叉插入另一只的袖管里,有时候还故意嘻皮笑脸倚着门框,装出一副地保的样子。这模样太讨人喜欢了,他看见总忍不住将她抱在怀中,说你呀怎么还像个孩子。
其实两人都老大不小了,他自己还要比春离年长一些。但那两年里他们在小楼上过的日子甜蜜,终日嘻嘻哈哈,或是春离老在蹦蹦跳跳,还真像两个不识愁烦的大孩子。可这一切当然是虚的,昨晚上的欢爱中春离便忽然感觉到忧伤像羊水似的,从她身体内某个破口汩汩溢出,她没声张,咬着唇于静默中潺潺落泪。那性爱仍于黑暗中进行,待他发现春离在哭,才吓了一跳,欢事戛然停止。
他以为自己把她弄疼了,天,有那么疼吗?春离脸上满是泪痕,而她见他停下来,晓得再也隐藏不了,终于忍不住放声,躺在那里嘤嘤地抽泣。
终是一整晚哭到头了,蜡炬成灰泪始干,今天春离肿着两眼,神情总是木木的。看着他背着行囊,拖着那样硕大沉重的行李箱,笨拙地努力要全身进入电梯里,她始终没上去帮忙,甚至没有响应他一句“保重”或“路上小心”之类的话。直至电梯门合上,他在里头喊了一声,春离!春离还抱着手在那里怔了一阵。她心里在数着,十楼,九楼,八楼,七,六……
数到“一”以后,她想象着他如何费劲地把行李拖出电梯。离开这座楼以后,还得沿着院里蜿蜒的石板小径走上一段路,才到得了大门口。春离等了一会儿,回过身锁上两重门。她心里早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去看这一眼,可她心绪不定,在厅里胡乱踱步,颤着手用食指猛弹拇指的指甲。以为已经被泪水消耗殆尽的悲伤,突然迸出一股暗涌,又在她体内涨满。春离哭喊了一声,拔腿冲进卧房,直跳到小小的窗台上。像个孩子似的,两掌贴上窗玻璃,额头也抵上去了,睁大着眼睛看着小区门外沙尘飞扬的路上,一辆出租车缓缓离开。──《短歌》)
《短歌》的场景是一个叫原乡的大陆,地点却还是在这城里。你其实读它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女人的描写十分细致,那个带窗台的小房子俨然是你父亲在内地的诸多小投资之一,多年来出租给不同的租户。有一年房子被发展商高价收购,你随同父亲到过那里,帮忙他把房子清空。
那时候,女人当然已经不在了。小说中的春离最终把房子的钥匙放在床上,自己带着个孤零零的喜字钥匙扣离开那里。她会到哪里去呢?她总有下一篇小说可以寄居。而下一篇小说总是在这城里的,你游目四顾,街上每一个女人都有她的影子或有一点她的特质,连一个背着书包走过的女孩也隐约蕴含着女人的孩提时代。你明明晓得她在这城里,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象征着她,但她的自我分解意味着她在真实世界中逐渐消失,你无法从这些分散的特质里重新把她提炼出来。
但在许多的小说人物中,你相信总有谁从女人那里获得更多的配给。毕竟这是一种不可能均匀的自我复制,总有谁继承了更多她的背景身世,有谁分得了更多她亲身经历的事,有谁遇上更多她遇上过的人,有谁享有了更多她的欢悦与良善,有谁分担了更多她的恐惧、痛楚、罪恶。在众多人物里面,也必然有谁的肉身长得与她最酷似。
因为你如此坚定地相信,那女人便因应你的目光,从她的小说里走出来。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你在流动的景观里看见她,像是在一片黑压压的群体里无可避免地看见了一个发光体。女人站在对街,她身后是一家已经不该存在的杂货店,老旧的铺子里黑压压地填满了各种堆栈整齐,但几乎已完全褪色的物事,譬如藤编的簸箕、篮子,宽檐帽和葵扇;绘了旗袍美人图的铁牌挂历和煤油灯,黑胶唱片和卡式录音带……所有对象连同那店铺都只剩下黑白色调,泛着点点焦黄,像是熏染在岁月表皮上的灼痕。
雨越下越大,女人抬头看了看天,倏地举起两臂,于空中撑开一把红艳艳的雨伞。在这天色逐日暗沉的街上,她的雨伞看着像一把熊熊的烈火。整条街上的人都看见了,每个匆忙赶路的人视野里都有一树火焰盛放。真招摇。你马上认出她来,她是她自己笔下的小说人物,很可能是某部短篇里那个每朝坐在窗台上遥望长街并痴恋着某个美少年的女人。
她也立即意识到你了,因你浑身透着一种不属于这小说的味道。这街道上行人如潮水奔泻,人们无语,车不响笛,但街面总有一种听不见的巨大的喧嚣。你站在对街,倚靠着一根光秃秃的电线杆,穿着带帽子的防水外套,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在那里,人们把头颅微微缩到双肩里急步从你身边绕过去。她想不起自己在哪一篇小说里写过你这样的人,莫非你在小说里只是个孩童,后来从一部完成了的小说里出走,独自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长大,慢慢完成自己。
但女人知道你不是她灵魂的隐患,并非因你已不再是小说里的人物,而是她已经不再是写小说时的自己了。她在那些年的书写中把自己一点点掰碎,再小心翼翼地把碎块和粉屑揉入重重的虚构和真实中,直至她完成她能写的全部小说以后,“自己”也就不复存在,而成为许多个小说人物从不同角度投射的影子。
“这只是小说,不是真的。”她揉一揉左眼,再揉揉另一只,把你从她的小说世界里涂抹掉。
你于焉在雨中隐去。
●
现在,女人看见的是伞沿垂挂着整齐的雨帘,雨帘外面依然是满目的雨。雨声碎碎的,城市随着她把脖颈伸长而迅速起立,周围的大楼把灰蒙蒙的天空高高举起,她便觉得这里像个峡谷,或一口深井。天注下雨来,亿万颗水珠淅淅沥沥,在柏油路面,在车顶,在人们灰扑扑的雨衣和暗沉沉的雨伞上相继碎开,街上腾着雾一样白茫茫的水汽。
在她写过的小说里,如果有故事,便总是少不了这样的雨。
少不了一条瘦骨嶙峋或跛了一足的癞皮狗在单向道上逆向行走,它浑身湿嗒嗒但已经无所谓了。这野狗夹在下班的人潮里等候行人灯转绿了才跚跚地越过马路,它在这城里活得多么老练,经过她身边时还似乎睨了她一眼,那对望里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意思,这城市就这样子,建筑物过度堆栈,人们无处可寄,都像难民似的全被挤到街上,除了每一个路口的红灯、绿灯、黄灯,其它的如同小说里所写,总是一幅惨淡的几乎无色的景致。
雨是那样无尽怨尤如泣如诉的雨,所有的故事都十分潮湿。为什么这样呢?现在的雨已经与季候风无关,她记得以前,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雨的往复可以计算和预期,譬如四月清明,九月皇爷诞,雨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的雨,而今却像她40岁后连续数年的欲潮般荒淫无度,昼夜不分,断断续续却又连绵不绝,再也说不清楚这算是上一场雨的后续抑或是下一场雨的序曲。
当时她那么年轻,创作力惊人,想象力丰沛,可以用不同的故事去标记每一场雨,或者用不同的雨去记载每一个故事。而今她韶华不再,记忆力衰退,老觉得思维黏稠,脑袋里堵满了淤泥。便越来越频常也愈渐清晰地听觉到那远去的世界传来的语音。雨变得再无特点,像她所住的这城市一样没了个性。有时候她会怀疑,此城是因为过去那些年被她翻来覆去地书写,才逐渐失去它的风情,变成如今这典型的城市的样子。要不是还有这颇不寻常却也早被人们习以为常的雨,这城还有被人们记住的价值和需要吗?它如今还会不会在地图上有个小针头那样的立足之地?
她甚至偶尔也怀疑,这些年来身边那些相继去世的人,多是被她的笔所诅咒过的。她的父母朋友同事,她的爱人与伴侣。她活着总忍不住想象这些人的厄运、劫难与消亡,再以他们的不幸去把故事引伸开来。父亲自然是最常投影到她的作品里的人了,因而他死前受尽折磨,死时孤苦无依。再来便是那在远方的男人。她其实从不曾直接写他,但她知道他的身影总在字里行间出没,高挑瘦削,背微驼,有许多名字和代称,却又往往面目模糊──起初被她千回百转地刻意隐去,后来因时间像书本里的蠹虫,将她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秘密慢慢蛀空,她几乎不自觉,竟从此记不清楚男人的面容。
但女人知道终有一日她是会想起来的,也许会在她弥留的时候,那些失落在脑中各处如珍珠般的记忆,终会一一浮现并自动串连。会那样吗?会的。她在好些小说里写过这种事,而如果真的如此,那远方的男人在生命最终的一瞬,想必也曾看到她了,看到混沌中慢慢清晰起来的,那些年美好的种种。
●
你看着女人双眼睁开,却像个梦游者似的在街上行走。她头顶上的红雨伞好大一篷,常常会压下来,不知道挡住了的是她的脸抑或是你的视线。但那红色总算是个醒目的记号,让她在这小说世界里无所遁形。她在街的那一边,你在这一边走,路上的车子很多,仿佛隔着一道真实与虚构之间的鸿沟。但起码在这一刻,你们的世界是平行的。
女人没发现你,你不是已经被她从小说里抹除了吗?在这城里无所谓出发也无所谓归去,她只能沿着脚下的人行道去模拟生活的步伐。这条路上没有很好的风景,右边是大河一样永远车流汹涌的六车道主干路,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完全找不着可以让人横越公路的行人桥和斑马线;另一边彻头彻尾是一道不中断的画满涂鸦的墙壁,据说那是一座老监狱的围墙,因此除了入口大门的两扇铁闸以外,它几乎是一道无穷尽的“口”形墙。
女人真想不起来自己在哪个小说里写过这样的一座监狱。她曾经想过哪一天要沿着墙根走一圈,慢慢把画在墙上的图画看个全。这面墙上画的东西乏善可陈,无非是些挤成一堆的空心字体与线条粗糙的人形画像,有的在咒骂,有的在嘲笑,有的在卖广告,有的在宣教,善与恶在互相抵消。神爱世人,去你妈的,男人救星至尊妙药无效100%退钱,地球人去死,南无阿弥陀佛,合法贷款电话1234567,陈XX我操你全家……
自从女人停笔不再写小说以后,每次走在路上都会身不由己地走到这一带这一条路上来。这墙上的涂鸦已让她感到厌倦烦腻,她会去想象这围墙的其余三面。记得曾经有一个自称来自真耶稣教会的教徒在这路上对她穷追不舍,一边宣教一边说起这围墙的故事。据说以前这城里没整日下雨的时候,曾经有个囚犯沿着这墙画了一幅世上最长的壁画,可尚未来得及把四面墙都画满,那人便刑满出狱,以后他虽主动请求完成这壁画,甚至愿意自己掏钱买工具和漆料,却直至他后来患癌病终仍不获批准。
这样的故事假作唏嘘,其实充满了宿命论与恐吓的意味,编撰手法与那教徒传教的惯技一样的拙劣。他总是一个劲要说服你让你相信活着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你的生命不圆满,你不快乐。女人不胜其烦,她加快脚步在雨中疾走,红雨伞像一面巨大的盾牌在街上左支右绌地乱晃,不知在抵挡着什么。那位真耶稣教徒虽没有紧跟上来,却叉开腿当街高喊,没有用!你逃不了的!天国近了!
有过那次经历以后,女人每次再经过这路上,都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她拿红雨伞掩护自己,她的红雨伞无论去到哪里都挂着一串串的雨,那是一把招雨的伞,像她那一支下咒的笔。压在雨伞上空的不是真耶稣所预言的天国,而是烟雾般悬浮在空中的记忆。她举起头,那上面永远有个女子在俯瞰,手掌与额头抵在窗玻璃上,永远像个不甘心的孩子。女人知道那只是小说里虚构的画面,但在这城中,小说虽然总是充满偏见,却是凌驾所有真实的最诚实的供述者。它们分明是那样对女人说的,没有用,你逃不了。
如同雨,女人在这城中无论去到哪个角落都会听见真耶稣的吆喝。你逃不了,你不快乐。此刻她就听到了这像风一样萦回不去的声音,这让她裹足不前,忽然搞不清楚自己身处哪一篇小说中,又该往哪一个故事走去。这里所有的小说都有了定局,她深悉自己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无常”实际蕴含的机关,以及命运与命运之间细微的衔接。
这真让人丧气。女人还想着或许该绕过去看看其余三面墙壁上的风景,但今天这雨下得像浆糊一样叫人提不起劲,她顺着路走,鞋子全湿了,衣裳上全是雨给的鞭痕。她觉得累,忽然想回家,那路旁便有了一个候车亭。那里等车的人很多,女人试着想挤到亭子里,但没有人愿意给她挪一挪。她实在没办法,只有撑着伞站到亭子外面去。这雨让一亭子的人动弹不得,有一条尚未跛足的癞皮狗叼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根大骨头施施然走过,饶有兴致地边走边打量着挤在候车亭里的每一张脸孔。它的目光去到哪一张面孔上,那面孔便凝固在那里了。只有女人压下红雨伞挡住了脸,谁也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狗也没追究,无所谓地走过去了。
小说本就是这样设计的,她和人们会被画在一幅油画上,画布上的颜料涂抹得很厚,像早餐吐司面包上的巧克力榛果酱加黄油那样斑驳,而且笔触粗犷,每个人都分配到了微薄的存在空间,但谁也不能幸免,都得牺牲掉自己所有的质量和细节。
●
这一幅油画,此时挂在你家的墙上,就在玄关那里的鞋柜上方,正对着门口。画里一个挤满人的候车亭,营造了一种主要凭感受判断出来的雨境。许多双茫然而无特性的眼睛怔怔地盯着画框外头的世界;女人的红雨伞宛若盛开在暮色中的奇葩,孤零零的一株。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明媚,伞下的女人头也不抬。
你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这一幅画。那是父亲养病时在工作室里完成的作品。据母亲记忆,父亲年轻时因自觉天赋比不上别人而主动弃学,以后便谁也没见过他拿起画笔。后来患病不能工作,他在家里无所事事,倒是忽然有了绘画的念头。你见过他画这幅画时的情景,不知是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抑或是搁下画笔的时间太长,显然力不从心,稍有不满意便把自己关在房里生闷气,也说过罢了罢了这种像要放弃的话,没隔几天终是会回到摊开的画布前,安安静静地作画。如此反反复复,反正费时颇长,好不容易完成以后,他也就全没有了再画的兴致,那阵子倒是经常坐在画前发呆。之后病重,多在床上昏睡,直至终了。那幅画搁在工作室一隅,没引起谁的注意。
直至有一个假日家里大扫除,你去清理父亲的工作室,才想起处理遗物这回事。父亲生性节俭,是个精算着过日子的人,因此不太舍得丢弃。数十年来在非常简朴的生活里头,竟然也积攒了不少没有使用价值的零碎对象。其中一些东西,尽管物与物之间看不出什么联系,甚至有点不搭调,但它们被锁在铁制文件柜的同一个抽屉里,在你看来十分可疑。毕竟这些对象并没有被珍而重之地藏起来的属性──七本繁体字印刷,纸张略微发黄的小说集,一个原本用作包装茶具或花瓶之类的锦绣礼盒,里头放的却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包括被父亲用得不能再用了的两个手机(它们躺在盒子里,像两具标本一样的手机尸骸),来自某个遥远小国的几张纸钞和一把硬币,以及一个略嫌笨重,用起来很不灵活的方口带耳大杯,杯身绘了绿叶红花,如浑体刺青般华美。
你直觉这些对象是有些蹊跷的,尤其是那几本书,父亲没有把它们放在工作室的小书架上,没让它们与各种计算机绘图和精算学书籍、两本英文辞典以及一本十分老旧的世界地图集共处,而是在抽屉内自成世界,这点已经很不寻常了。再说七本书来自同一个作者,女性,那名字似乎寂寂无闻。你留意到书的出版日期隔着年份,扉页上有作者的亲笔签名与日期,既无抬头也别无留字,作者每回出书都想到给父亲送上一本,这心意却是可以意会的。
你知道父亲虽然爱好古诗词,因为学过中国画,对繁体字有点视觉审美上的情意结,甚至也亲自督促你学习中文,但他可从来不是个文学爱好者,也不是个会读小说的人,更无人听说他有个写作的朋友。这使得那七本来历不明的小说集更显得神秘暧昧,扉页上的无言多像水墨画中的留白,引人遐思,隐喻着许多未可告人之事。
每本书上的折页都附有作者简介,草草两三行字,说明作者来自某小岛,年龄比父亲小了几岁,专长小说创作,得过一些不算重要的文学奖。你只觉得她那小岛的名字念来拗口,像一串铃铛才能发出来的音节。你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念它,直至终于把它念顺口了,才发现这串发音像雨声,必须绵绵密密呢呢喃喃无穷无尽地念。而就在你如此练习的时候,窗外轰隆隆滚过一片震耳的雷响。那一年,在旱季持续了半年以后,终于在那一天下起了第一场滂沱大雨。
那年的雨季很不寻常,似是配合着你阅读的进度,雨拖拖拉拉地比往年延长了许多时日。书是沿着出版顺序一本接一本读的,女人的文字质感浓稠,叙述的调子缓慢拖沓,描写的文字远比叙事的文字超出太多,仿佛你看的不是书,而是许多串起来的静物画。而且画里用的是油彩,又像浸透了雨水似的永远油漆未干,让人读得呼吸困难,有一种类似泅泳者即将溺毙于大片珊瑚礁上那样的,绝美的无望。
你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的,也许是每一次要决定放弃的时候,你总会在字里行间发现端倪。你在好几部小说里瞥见了那一口绘着大朵红蔷薇的杯子;在两部相隔颇远的作品里看见了同一个钥匙扣的意象,它们的命运相同──两个一套,各自落单。
你甚至在某部小说里看见了自己。也许是《短歌》吧?(有个晚上男人喝了点酒,也许实在抑制不住,便对春离说起远方的孩子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了。男人很少提起那边的事,春离支着腮在听,眼睛虚应以微笑。因为看见他眼中的光芒和脸上抑制不住的骄傲,她心里既为他欢喜,却也感到漠漠的嫉妒……)
虽然小说总是在变换故事,里面的人物总是在更名换姓,也改变年龄和相貌,却是这些“物证”在不同的小说中相互参照彼此印证,如同线索串连着所有的故事。那女人什么都说了,却小心翼翼地一点也没说破。
●
你把左手从衣袋里伸出来,摊开掌心。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说还未完成。”
巴士车站里已经没几个人了。自从你走过去,冒着雨站在女人身旁,她便开始随机地把周遭的人一个一个地涂抹掉。她原以为你是真耶稣遣来向她宣布末日的另一个使者,但你的沉着、静默以及不属于这虚构世界的气质,让她很快明白了你不是她所创造的任何一个人物。你是按图索骥循迹而来的一个读者。她在伞下抬起头,其实雨已经停了,就只是她一个人的红雨伞仍然挂着密密麻麻的雨串。
女人叹了一口气,从你手中拿过那信物。
(一年前医生宣告了他的病,并请他们做好准备,她才终于按捺不住。有什么事要交待的吗?男人摇摇头,却同时把手伸到衣袋里,像在翻找他的钥匙。
想到男人当时隐忍的表情,她忽然心软了。于是她站起来,对男人说自己要上厕所,并把手里拿的一小包鸟饲交给那女人,说自己的丈夫神志不太清晰,请对方帮忙照看一下。
“十分钟,十分钟后我就回来。”
她走得不太远,却也不太近。十分钟以后准时回来,那女人把鸟饲还给她,也没说什么话便离开了。女人看来如此友善和从容,男人也依然无动于衷,以致她不得不怀疑这纯粹是个误会。至于数日以后,她发现男人的钥匙扣少了那半个“囍”字──由于男人压根儿忘记了那物事曾经存在,她也就无从追问了。──《钥匙扣》)
女人收起钥匙扣和她的雨伞。雨真的停了。小说真是那样写的吗?她有点不敢相信,站在那里看着除了你们以外空无一人的街道,路上的车子全都消失不见。对街的那一道象征监狱与囚牢的围墙依然横亘在原地,涂鸦依旧,乌鸦停在墙头。女人明白那是她的意志世界的边界,她既无法将之消除,也永远无法攀越。
关于牢狱以及世界的正反面,那是下一个小说的素材了。既然城里只剩下你们,而下一场雨还未赶上,女人挽住你的手臂,说走吧,我们沿着对面那道墙走一圈,看看那上面有没有你父亲留的字。
你没有反对。你知道在这虚幻的时间破灭以前,你们就只能拥有这点点奢华了。于是你们把脚步跨出去──尽管路上没有汽车行驶,就在跨出去的一刹那,你们的脚下生出了一道笔直的斑马线。
有了这斑马线,从别的故事中幸存下来的一条癞皮狗,跛着一足,也就从对面慢慢踱步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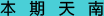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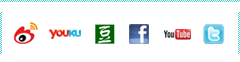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