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刊于《天南》文学双月刊第四期“情色异象”
“邂逅结束,辛巴达会回到唏嘘枝条丛里潮湿阴郁的墓地,一整年去听雨的鼓点;当鼓声也变得乏味,他会和墓穴周围死去的亲戚聊天。一个被蛆虫吃掉不少的叔公 试图在坟里咳嗽并翻个身。叔公在世时先后有过四任太太,同时一直和两三个女人保持暧昧,他等不及要找回肉身,叔公问蜘蛛,‘我想知道我疼爱的海伦现在好不 好,还没好好品尝她,我就死掉了。’
爱女人发狂的叔公焦躁不安,倒是让辛巴达找回一点生命的胃口。一个月夜,趁守墓人打开墓门,辛巴达溜出墓地,直奔他曾度过最幸福时日的地方。”
对20世纪匈牙利文学影响最深刻的作家,非汝洛·克鲁迪(Gyula Krúdy)莫属[1]。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认为,克鲁迪属于20世纪欧洲最伟大作家的行列。写作技法上,他的意识流略早于普鲁斯特,魔幻现实主义早于 众拉美作家;同时,克鲁迪风格独一无二,无法归类,后一点也得到美国作家亚瑟·菲利普斯的认同。[2]
克鲁迪1878年出生在匈牙利东北部,不到20岁时去了首都布达佩斯,发誓要成为诗人。30岁左右,他的写作风格逐渐明晰:一种游戏般地把讥讽与忧伤、怀 旧与现实糅合一体的文体。克鲁迪认为人是时间的奴仆,他瞄准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时间结构开刀,并看中了“梦”这一载体,梦能实现人和事件不受时间阻碍而自由 流动,“梦里梦外,人并非思考方式不同,而是记忆方式不同。”
匈牙利语现代文学创作在19世纪末渐成气候,1908年创刊的文学期刊《西方》有里程碑意义,克鲁迪是《西方》第一代作者之一。他在30~40岁间有过一 段黄金期,作品在各大报纸频繁连载。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创伤心理严重的匈牙利公众对缺乏时事关怀的克鲁迪急速失去兴趣。1933年,克鲁迪在极度贫困 中死去。
1940年代,作家马洛伊[3]虚构克鲁迪生命最后一天的小说《辛巴达归家记》出版,激发了年轻一代匈牙利人寻找克鲁迪旧作的兴趣。二战后,匈牙利被苏军 占领,新统治者宣称掌握“历史客观规律”,人们以阅读克鲁迪作为反抗,在克鲁迪文学世界的季节、天空、河流、树林、酒馆里怀念和保存那个“主观的匈牙 利”:
“这城市,像佩斯一侧河岸上漫步的女士,在春天里散溢紫罗兰的馨香。秋天,则是布达主奏的曲调;下落的栗子在城堡外道击出古怪的闷声,来自另一侧凉亭的军乐队演奏片段,飘曳在惆怅的寂静之上。布达和秋天,就是同一个母亲所生……”[4]
匈牙利学界在40多年苏占期里对克鲁迪的整理和重读,让“克鲁迪语言”和“克鲁迪情绪” 成为匈牙利现代文学的重要概念之一。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把克鲁迪当作其最喜爱的本国作家。
克鲁迪著述等身,《辛巴达》是认识他最好的首选读物。中欧大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辛巴达》系列短篇选译本,把此书称为“奥匈帝国的情色挽歌”。
跨越时空的情色旅行
从年轻时代到去世,克鲁迪一直没有停止过辛巴达系列的写作,辛巴达就是克鲁迪的“他我”。克鲁迪本人不仅作品多产,且生性风流,热爱赌博和美酒。小说主角 辛巴达是个风流旅行者,他认为世上只有女人值得自己为之而活,相信自己最能见证女性身上某种接近奇迹的品质,又确信爱情是女性用于俘获男性的罗网,他以谎 言为应对技巧。辛巴达看似始乱终弃的浪子,实际却是情色的囚徒,他抛弃和离开每个女人,又永久沉溺于女性魅力中,复而朝向她们追忆、寻找、回归。
《辛巴达》系列故事大都发生在辛巴达死后。他有时300岁,有时是鬼,有时人鬼混淆。旅行、寻找和回忆,对辛巴达是同一件事。他的怀念不是单纯追溯,而是
寻找,寻找即怀念。他怀念的不是翻云覆雨的性爱,也不是誓词和谎言,他怀念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他喜欢女人的腿和长袜,喜欢女性率真的话语,也喜欢和
她们说话,辛巴达在冬日里找到昔日情人葆拉,他说,“我梦见你在梦我,我就出发了。”
约翰·卢卡奇借物理学概念提出:克鲁迪是“四维写作”,他对现实主义小说时间结构的否定,让时间维度在《辛巴达》等作品中展现。《辛巴达》中,生死退到情
色之后,生死间界限消融。“在辛巴达的多次死亡过程里……他重新造访那些他曾感到特别幸福或不幸的地点。”[p5] (《孩童的眼睛》)
中国古训以人死后的骷髅形骸来告诫花痴淫徒——辛巴达截然相反,“世间唯女人值得我为之而活” (《鹳》)。——是死鬼还是活人,不改变他对女性魂萦梦牵,他在生死混淆中持续旅行,造访被他抛弃却仍深爱他、对他有怨、或曾把他囚禁在密室做“爱奴”的 女人,他和她之间是梦境般的对话:
以短篇《辛巴达的梦》为例:
辛巴达300岁,感觉快死了,突然想去看望老情人“猴子”。“所有爱过她的人都管这寡妇叫‘猴子’。她是个认真、有主见的女人,富有毅力,因为女人通常会在更换情人时改变昵称,她却自始至终叫‘猴子’。”
“猴子”深爱辛巴达,几十年只读辛巴达推荐的保罗德科克[5]巴黎情爱小说,
“有时候我是如此爱你,我感觉不像你的情人——你抛弃、远离和遗忘的情人——更像你的母亲。我如此了解你,像我曾把你生出来。”
同时,“猴子”告诫辛巴达,必须了解女人的毁灭倾向,其表现形式正是爱情。
“上帝,若是男人像我一样了解女人,那些关于爱情的荒唐对话将不复存在。亲爱的,你得明白,女人是慈悲一击[6]的产物。越年轻的越糟糕。记住,我不会信任任何一个女人,哪怕是老女人。女人的脑子里总是装着毁灭,她编织着爱情的圈套,只为毁灭男人。”
告诫对辛巴达不起作用。他当然能察觉女人的毁灭倾向,但怀疑毫不改变他把女人当作自己存在的意义。男和女,正是这样不可互解又永远在交流,不可调和却互为存在理由。
辛巴达告别“猴子”回家,临死前的早晨,眼前浮现的全是女人身体,
“女人的脸,帽檐下的脸和无帽的脸,化妆的脸和无妆的脸;女人的眼睛,女孩的眼睛,全盯着他,仿佛辛巴达是世上仅存的男人;裸露的肩膀和高跟鞋上方裹着长 袜的腿;然后是一列只穿内衣的女人,辛巴达认识的,或他想认识的;丰腴的臂膀,纤弱的臂膀,每只绕过他颈部的臂膀……”
作为对“猴子”坚持和坦白的回报,辛巴达让她见证自己死。辛巴达派人送信给“猴子” 。但他们间没有生离死别的“悲情”,克鲁迪只写了一句话,
“‘猴子’很快来了,轻柔地为辛巴达合上眼睛。”
辛巴达的死仅是他和“猴子”之间相遇再分别的交点,死去的辛巴达自由走向寻找女性的旅程,他考虑过变成一把梳子,但害怕落入不爱清洁的女人手中。于是,他 变成玫瑰花环上一枝槲寄生,但把他放在腰间的是个老尼姑。辛巴达受不了她的成天祈祷,幸运地掉到火车铁轨间,“火车驶过,养路工撒过炽热的煤灰,一块油纸 包着被人反复嚼过的鸭腿飞到他身边,这个新邻居试图和辛巴达发生某种关系,但辛巴达假装睡着,趁夜晚来临溜进城里。”
他认出这小城,城里一个掘金者的太太曾是辛巴达在佩斯城的相好,她嫁给掘金者前,曾吻着辛巴达说,等她老去时,若辛巴达仍觉得她有魅力,可以来找她。
看她在镜前梳头,梳子像船只航行在她波浪一样的金发间,“我其实本可以做把梳子”,辛巴达又想。
死去是一个情色过程
《辛巴达》系列短篇中,作者总觉得辛巴达死一次不够,安排他反复死亡:有300岁时终结死:“终于他意识到,既然都已经历世上可经历的一切,他将很快死
去。” (《辛巴达的梦》)也有自杀:“辛巴达在一个秋日里离开他自杀后被安放的墓穴。”(《夜晚访客》)有时死因不明,但死前和守墓人签过协议,让他有一次短暂起身的机会,“守墓人查看了协议,几分钟后,一个穿着紫色夹克、神情忧郁的黑发年
轻人出现在垂柳之下,缓步走向正在捡起(母亲)坟上枯叶的女孩。”(《墓下疯狂》)
卡尔维诺认为,短篇小说重复的终极含义具有两面:死亡无法避免,生活在继续——克鲁迪《辛巴达》完全相反:生活无法避免,死亡在重复和继续。有时辛巴达故事的前提即死亡,“在死去并变得睿智以后,辛巴达重返红犉客栈……” (《红犉客栈》)
《西方》是最早介绍克尔凯戈尔的匈牙利期刊,20世纪匈牙利文学几乎与生俱来拥有存在主义色彩,克鲁迪的作品有不少展示。但克鲁迪的写作又从不越出文学边 界,若“存在主义”是19~20世纪哲学、神学等领域的新概念,“存在”却从来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如马洛伊所说,“文学里只有被重新注入活力的概念,不存 在新概念。”[7]
克鲁迪另一部作品《太阳花》的英译者约翰·巴特基[8],曾找到1917年克鲁迪写给即将连载《太阳花》的报纸的信,“我致力于一部现代匈牙利小说,但其 内容就像这里的土壤一样古老……这小说背后隐藏着一种古老的欲望,在那种久违的专注力中蛰伏的潜能。还有,一股来自墓地的鬼祟微风轻推着我:你死后将留下 什么?……因此,让我们看看你在那段自认为智慧、冷静和沉着的时光之后到底有什么存留。”
从此信出发,巴特基讨论了克鲁迪作品中的欧洲大陆原始女神崇拜痕迹,认为他的晚期作品尤其具有人类学研究价值。他参考考古学家金布塔斯[9]在《古代欧洲 的母神与神》(1982)与《母神语言》(1989)中的论述——古老的“大母神”具有三个特征:创造、毁灭和重生。“大母神”崇拜渐被后来的各路印欧文 化融合和取代。但金布塔斯认为,“古老欧洲的神化图景和标志从未完全根除……母神逐渐后撤至密林深处、山岭之巅。”
在克鲁迪故乡蒂萨河上游湿地,鸟被认为是女神化身,水禽如鸭,鹅,天鹅,苍鹭,白鹭和鹤代表女神快乐、丰腴和滋养的一面,猛禽如鹰,雕,鹰,猫头鹰,乌 鸦,乌鸦则是好战、死亡和毁灭的另一面,另外,猫头鹰和杜鹃是预言家。《太阳花》里的情爱故事仿若一个飘摇于河流水雾上的梦,其间鸟声不断,《辛巴达》里 也常有鸟儿(或飞兽)现身,短篇《墓下疯狂》里,辛巴达墓地上的猫头鹰对蝙蝠说,“为什么人总想着昨天?他们把整个一生用来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
且勿妄下结论说克鲁迪在寻根——“根”是表象的、民族的,不是世界的、本原的,匈牙利学界曾热衷于寻找马扎尔人来历(有人一度错误以为和中国古代匈奴有 关),克鲁迪对此无甚兴趣——世界并无“根”可寻,克鲁迪只关注“本原”,在他的写作中,时间与历史在死去活来的玩笑里被揉捏到次要位置,两者消失后,世 界重现其男和女的本原。
学者吉佳尼则认为,克鲁迪对性和死亡的探讨有弗洛伊德的痕迹,“但远非简单的理论套用,克鲁迪似乎更倾向于接受无情且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性是死亡的共谋。”[10]
克鲁迪同时代的众多匈牙利作家都致力关注男女情色与生死之间的内涵,像克鲁迪一样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卡林迪[11],代表作《卡皮拉利亚》讲述格里佛第六 次旅行,斯威夫特的小说主人公进入一个纯粹由女性统治的海底世界,见证了男性和女性的首次交配。 在卡皮拉利亚,矮小的男性一次次支起建筑,总在顷刻间被身体巨大的女性毁掉。《卡皮拉利亚》被悲观笼罩,或许和卡林迪写作同时正经历第二次不幸的婚姻有 关。相对而言,对婚姻和幸福都不抱幻想的克鲁迪在《辛巴达》里要超脱不少,对他来说,“幸福只是从欲望到悲伤的间歇时刻”。
《西方》第三代作家、文学史学者色尔伯在小说《旅人与月光》里有一段话,或许可以歪打正着地用来解读克鲁迪《辛巴达》之情色生死。
色尔伯杜撰了一位宗教史研究者瓦尔德海姆,他带小说主人公米哈利参观罗马的伊特拉斯坎文化展,后者对一列“男鬼牵引女人、女鬼牵引男人”的塑像产生兴趣。瓦尔德海姆论文《死亡的多种面貌》与此有关,他对米哈利说:
“这就是死亡,或者,死去,它们不是同一件事。伊特拉斯坎人完美地意识到……死去是一个情色过程,或者,一种性快感形式……对死亡的恐惧和欲望亲密地并存 在他们(古人)脑海,恐惧常是欲望的一种形式,欲望也常是恐惧的一种形式……我们作为情色的结果从女人那里出生,也不得不在女人的参与下于情色中死去,这 女人如同一个死亡交际花,其实也是大地母亲伟大又不可分割的另一面……谁知道,或许伊萨卡岛本就是死亡之地?在遥远的西方……而死人总在航行向西……或许 尤利西斯对伊萨卡岛的怀念和他的归途,是对‘非存在’的回归,即重生。或许佩内洛普的名字暗藏的‘鸭’含义,原本指的是神鸟,尽管我现在还无法肯定。” [12]
来自《一千零一夜》的“辛巴达”和尤利西斯一样也是航海者。辛巴达航行在怀旧里,世上只有女人值得他为之而活——他常说谎要女人和他一起死,却极少对女人 痴情至死,殉情是爱情故事,而非克鲁迪讨论的情色本原——情人法妮要求辛巴达实现誓词,和他一起为爱而死,辛巴达略带疑虑地回答,“我认识死亡。死亡属于 女人。”(《逃离死亡》)
译作生在没有疆域的想象国
亚瑟·菲利普斯在《太阳花》英译本出版时直呼,克鲁迪作品译成英文太少,实在不过瘾。但匈牙利语译成英语,却非易事。
属于乌拉尔语系的匈牙利语是个孤儿。在中欧地图可见,匈牙利语周围是印欧语系的包围圈:斯拉夫语、日耳曼语、拉丁罗曼语。匈牙利学界早就意识到本国语言的
“孤独”,这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尤成障碍——捷克作家找不到合适词汇,常可从同属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和俄语中借取。匈语作家却无邻居相助,同属乌拉尔语系的
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与匈牙利语历史隔膜太久,唯语言学家才能看懂。
“孤独”处境促使匈牙利文学界勤于翻译欧陆经典,大量新词经改造整合融入匈牙利语,德语等外语句法被借用。20世纪初,几代《西方》作家成果灿烂的创作, 实际也是宣告现代匈牙利语的成熟。匈牙利文学界严谨、勤奋的翻译传统甚至在苏俄霸权笼罩下也未中断,《辛巴达》译者斯尔特西[13]在1980年代中期重 返匈牙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所遇到的作家都在从事翻译。
其时,斯尔特西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布达佩斯之旅让他开始投身翻译,此后近30年,翻译工作一直平行于诗歌创作。1995年,斯尔特西翻译匈牙利女诗人拉科夫斯基的作品《新生》获“欧洲诗歌翻译奖”。
《辛巴达》是斯尔特西迄今为止翻译的16部匈牙利文学作品之一。若斯尔特西可自选,他宁愿译诗而不是小说,译诗更考究,更贴近其内心,且全世界从事翻译匈 语诗歌英译的或许只有五六人而已。可惜,译小说,总是出版商找他,而译诗,需要他去找出版商,“我的翻译工作正面临小说把诗歌挤走的风险。”
罗伯特·佛洛斯特说,“诗歌就是翻译所遗失的部分”。斯尔特西看法不太一样,“若译者精熟于接收语言的诗歌体系,翻译中遗失的部分也能稍稍弥补回来……哪 怕在母语中,诗在不同读者中的回响也不同。优秀的诗歌翻译,是把充满回响的阅读用另一种语言写成回响出色的诗歌……译作,生在没有疆界的想象国。”
德国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数量甚为可观。两国地域临近,历史上德、匈双语母语人口数量不少。此外,德国文学界也有良好的翻译传统。匈牙利作家马洛伊任《法兰 克福时报》驻巴黎记者六年之久,流亡意大利和美国后,几乎只有德国持续翻译出版他的作品。法国对匈牙利文学也有较多翻译,之后是意大利和西班牙。
斯尔特西遗憾英伦缺欧陆的翻译风气。实际情况是,整个英语世界与匈牙利乃至中欧的文学态度始终有隔膜——以色列作家奥兹2010年访问匈牙利时说,英美文学离不开“娱乐大众的需求”——或许这是匈牙利文学长期被冷落的重要原因,英语世界出版驱动力是市场。
克鲁迪作品最初的英译本靠匈牙利图书基金赞助,在匈牙利本国出版。1997年科尔维纳出版社出《太阳花》英译本,1998年中欧大学出《辛巴达》英文选译 本,1999年,诺然丛书出克鲁迪短篇英文选译《梦骑士》。直到2007年,美国纽约评论丛书才购下《太阳花》英译本版权,2010年,《生活是场梦》加 入企鹅“现代经典”系列。
马洛伊是英语世界认可最多的匈牙利作家,促因是小说《余烬》1999年在德国再版卖出20万册。仓促中难觅合适匈语译者,英文版《余烬》竟直接从德文版转 译,之后斯尔特西才受邀翻译马洛伊其他作品。英国普希金出版社擅长出版不受英语世界重视的欧陆名家(如茨威格),90年代末出版色尔伯《旅人与月光》,也 因该书在意大利热卖。他们采纳英国诗人里克斯[14]此前十年斟酌完成的翻译佳作,竟有编辑以“可读性”为由,试图说服里克斯删掉所有副词!
从翻译本身看,匈牙利文学译成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更自然,这些接收语言有较好的屈折性,文学作品在新语言中容易找到前后一致的结构性和节奏感。英语不 然,它是最缺乏屈折性的印欧语,且英语世界地域宏大、变化快速、区域差异明显,现代英语作为一门文学语言尤其任性难把握,如亚瑟·菲利普斯对《太阳花》英 译本的批评,“19世纪英语开头,20世纪50年代英语结尾”。
匈牙利语语法系统和印欧语迥异,克鲁迪用词和句法更是独特,约翰·卢卡奇一度悲观认定克鲁迪“不可译”。巴特基承认着手翻译克鲁迪时试图“译成现代英语” 的困境,后来发现,最适合英译克鲁迪的或许是某种19世纪诗体语言,例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里克斯等译者也表示,匈牙利语 译成英语,最易丧失原著的音律性。里克斯甚至认为,好译作须具备一个潜在功能:刺激读者去寻找和阅读原文。
诗人做翻译,或许是匈牙利文学进入英语唯一合适的出路。从另一角度看,也须承认最能帮助文学传播普及的恰是英译本,这又得归功于英语图书市场发达,小说类 出版物印数通常不少,旧书交易成气候。克鲁迪、马洛伊、色尔伯等人的英译本一面世,很快在网上能廉价淘到二手书,能与之相比的唯德语图书。相反,他们的法 语、意大利语译本只能从网络或书店以不菲原价购买,或是在图书馆找到,另有印量极少的译本,已难觅踪迹。
Gyula Krúdy, The Adventures of Sindbad,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Szirtes, Budapest-London: CEU Press, 1998, ISBN: 9639116122.
[1]匈牙利语人名先姓后名,但写入外语时习惯欧式先名后姓。本文跟从这一惯例也采用先名后姓:,Gyula是名,Krúdy是姓。
[2]Arthur Phillips, “ Exquisite journey”, in Arthur Phillips, LA Time, August 26, 2007 .
[3] Sándor Márai (1900~-1989),襄多尔·马洛伊(港译桑多·马芮),匈牙利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曾游历西欧多国,是最早为卡夫卡写书评的人,坚定地反法西 斯,二战后遭当权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捷尔吉·卢卡奇公开批判,流亡意大利,1989年在美国圣迭戈自杀。马洛伊死后数月,匈牙利解放,匈文学 院恢复其院士资格,作品再获出版,对马洛伊的纪念活动持续至今。
[4] 引文来自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ács)发表于1986年12月1日《纽约客》介绍克鲁迪生平的文章,“The Sound of a Cello”, 请见1986年12月1日《纽约客》;这段文字来自约翰·卢卡奇自译,Gyula Krúdy克鲁迪作品原文出处待查。
[5] 查尔斯·保罗德科克(Charles Paul de Kock(1793~1871),法国作家。,1793-1871
[6] 原文“coup de grâce”为,法语,意指战场上对受重伤已无救的战友或敌人最后一击,以结束其痛苦。
[7] 《Mémoires de Hongrie》, Sándor Márai, Föld, föld,,,! 法译本 Albin Michel, Mémoires de Hongrie., translated by George Kassai, Albin Michel, 2004.
[8] John Bátki,幼年随父母逃亡美国,后成为英语小说家,诗人,翻译家。
[9] Marija Gimbutas (1921 –1994),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出生在立陶宛,二战后流亡美国,在神话学、古代印欧语等领域有过杰出贡献。
[10] Lóránt Czigány,,《A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mid-197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 Frigyes Karinthy(1887-1939),匈牙利20世纪初匈牙利重要作家、剧作家、诗人、记者和翻译家。
[12] Antal Szerb (1901-1945),文学史学者,小说家,代表作包括《旅人与月光》、《龙首传奇》、《王后的项链》。《旅人和月光》, (Utas és holdvilág,), Antal Szerb 1937. 英译本:Journey by Moonlight, 2001, Pushkin Press, translated by Len Rix, Pushkin Press, 2001.
[13] George Szirtes ,(1948-)出生于在布达佩斯,后1956年随父母逃亡英国,后成为英语诗人、翻译家者。
[14] Len Rix,1942年出生于在津巴布韦,诗人,文艺评论家。从大学教职退休后自学匈牙利语并从事翻译,多项译作受到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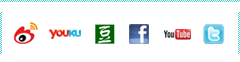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