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翻译:btr
摄影:徐军
1987年,您首次来中国。至今您一共来过中国多少次?
可能这已经是第20次了。我已经有两年没有来了,按北京时间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北京每个月都在变化。
这次您来感觉有什么不同?
总是很不一样。不是那种令人震惊的不同,不像那些十多年没有来这儿的人,但总还是不一样。通常我去北京和上海。有一年我去了安徽,一个叫黄村的小镇(不是 人人都是去的那个文化景点。没人去那儿。那儿离黄山大约一小时车程。)我住在一个有4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因此我明白了活在40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那 是清明时节,天气很冷。
您喜欢那儿么?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到那儿时正好清明时节。我们可以跟着人们上山,他们在那儿做清明的仪式。其实并不真的是清明那天,但有位老妇人死了,因此女儿要做一 个礼拜的仪式。他们做了一个大的纸房子,然后烧掉。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我们给他们看在美国人们是如何做清明的,那些东西很难看。但他们的清明祭祀物品 就很美。随后我又到了北京,因为我的叔叔葬在八宝山公墓。
您非常喜欢传统的中国。在《喜福会》里,您描述了女儿是如何把自己手臂上的肉割下,放进汤里,以便治愈她的母亲。
对,对。因为我外婆那样做。那是真实的故事。那是种自我牺牲的传统。那时是1922年,或许1923年。我的母亲和外婆住在上海,大概在崇明岛。
美国读者肯定觉得这很有异域风情?
我也这么觉得。是我母亲告诉我这故事的。我希望她不要求我也这样做。
在某个采访中您曾提到,当你来中国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多美国。现在还是这样吗?
不像以前那样觉得了。因为中国的文化已经那样“西化”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称之为“西化”),许多正在这儿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举例来说,以前没有人付小 费。几年之后,是的,你需要付小费了。那时我们和另一个美国人在一起,他说“不,不,你不用付小费”。但我说“不,你需要”。我的意思是,就是有那样一点 不同了。在中国,人们对什么都不惊讶。他们了解西方文化。他们理解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我总是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因此我四处活动很方便。但我想,也许其他 美国人会惊讶于中国如此摩登。我住过的世界上最时髦的酒店就在北京,在三里屯的瑜舍。

还有人误认为您是韩国人吗?
会吗?有时人们以为我来自台湾。或者⋯⋯我也不知道⋯⋯也许以为我从韩国来。我是华人,但又不那么华人。区别在于,在1987年,人们会盯着我看,因为我 看起来像中国人,但他们可以分辨出我不是。因为我穿着裙子,长头发,化了妆⋯⋯ 我甚至被误认为是妓女。他们对我说着中文。那时我在青岛一间酒店的酒吧里。所以说一切正在改变。改变得如此之快。到1991年,就没人盯着我看了,因为人 人都穿着更加时髦的衣服。很相像了。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曾和几个朋友在三里屯看人来人往。他们会说,“这是德国人”,然后有人走过,他们会说“这些是 中国人”,“那些是美国人”⋯⋯ 看到底是哪里人很有意思。如今在中国,人们混杂一处。这也是不同之处。
那您认为典型的美国特质是怎样的?
他们更加随意,以某种方式。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是你的举手投足,令人们可以立刻分辨。有一种衣着风格。年轻人背着背包。有点乱糟糟的,相比之下德国人就很 整洁。我讲不确切。总而言之,美国人挺友好的,但我们觉得他们不太了解中国。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很久以前。明年3月,我会在上海和一些朋友见面(我们要 去印尼,但会在上海停留),然后他们就问该如何预定机票。我说“就联络你平时那个旅行代理商咯”。就和去其他地方一样。就是那种感知很麻烦。我开玩笑说, 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就像“共产主义的香格里拉”一样,他们吃不准到底是个很有异域风情的地方还是共产主义。而美国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很容易接近,很简 单。
我曾贴了张照片说“这是上海20年前,而这是上海的今天”,你知道那里有非常有意思的浦东天际线,然后就有人说“噢!太悲剧了。空气污染真糟糕。”我想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停留在过去。
你是把照片发在网络上的吗?您用电脑写作吗?
对,我用。我用facebook,我用VPN就可以上。你经常到这儿来就会懂得怎么搞定这些事。让人们来中国把自己的理解带回去,会更新他们的认识。我在 facebook上与人们交谈后就意识到他们对于中国的感知是那样局限。他们不可能读一本书就了解中国。我想他们需要到这儿来。他们会惊讶的。这儿的建筑 比他们曾经看见过的都宏伟。那样与众不同。
我也有一次非常不同的经历。我去了贵州,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去了好几次,加起来住了有三周。那个村庄叫东村,离贵阳差不多八小时路。我乘了很久巴士,然 后上山。他们是种植稻米的农民。非常非常贫困,我去那儿写一个故事。写一个故事意味着要去那儿,真正地理解那个地方,他们相信什么,对于风水的感觉,如何 平衡事物,而不是写那些不平常的事。不要将美国式想法加诸其上。我觉得那是我去过的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但那也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您去中国的这些地方,是为您的小说做研究吗?
那是为《国家地理》所写的文章。是一个约稿,但我选择了地点。他们问了我好几次“能不能为我们写点东西”于是我就去了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一直想 做一个生态博物馆,来保存文化。你知道,在很多地方,年轻人都在离开,旧的传统丧失了。他们正试图保存那些歌。歌曲也流失了。没有被写下来。因此他们想把 歌录下来。于是我去了那儿。非常美丽的建筑。然而在上次和下次去之间失了一次火。而这就是我的故事:当这些人们失去家园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一切都没 了,他们失去了母亲,珠宝,一切。没有保险。因此他们所做的是成立社区,拾起一切从头再来。我就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在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和我讲故事。 那是个小村庄。不只是问问“你吃饭了没有”,而是在我说“好的”的时候,他们会说,“好吧,那就来我家午餐或晚餐。”他们希望我过去,那样就可以把故事告 诉我。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信任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很多趟。
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是如何与您的小说写作相关联的呢?
非虚构写作有更多关于长度的限制。我不能超过比如说1000个词。这令我自动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上。我需要把事实弄正确,确保没有说什么不正确的东西。 我也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让别人尴尬的东西。因此写那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会有责任感。我必须意识到,他们认为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公共的。 写小说的时候,我不需要考虑这些。我可以虚构,我不用担心它有多长。我可以杜撰一些私人的故事。如果我写杀害另一个人,我也不用担心(笑)透露他的名字或 诸如此类的事。

您上一本小说出版至今已有六年。听说快有新小说问世了?
对,我总是对不同世代的人感兴趣。但这并不因为我对世代本身感兴趣。我一直好奇的,是通过一代一代人传给我的东西,人们知道会受父母的影响。但有时候,他 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父母会被他们生活的时代所型塑,会有社会学的或是政治上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父母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受所失去的东西的影响,受他们生活的那 个时代的婚姻的影响。就这样我明白了我外婆对我母亲的影响。有些东西从我所有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下来。而那便是一部分的我。从那种意义上说,它与一种中国 的生活相关。我外婆一度是一个妾。她自杀了。所以她是怎样感觉的,她所处的时代如何,她的性格如何?我看着我母亲,又看着我自己。你永远不会让自己比别人 糟糕。在你的生活里,你没有发言权。一切,包括你该如何感觉,都已经被决定了。她也有坏脾气。而我发火的理由总是和我母亲及我外婆一样。(比如说?)比如 说不诚实,或怀有优越感地假惺惺示好。那会让我很生气。
您在早期的小说里写了不少母女冲突。现在您对您父母是否有了更多的同理心?您对母女关系的想法在这些年里是否有变化?
依旧继续着。我写我所信的,因为我与母亲的冲突关乎她的信仰,我是否应该遵从她,为什么,以及她总有的危机感。为什么她会那样感觉?而我希望过一种不必忧 虑任何事的生活。我可以看到,当我开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把自己放进她的生活,于是我做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背景:她的丈夫是谁,为什么她不能离开自己的 婚姻。于是我谈论那时候发生的事,战争,害怕我不听她的意见或没有她的指导便擅作决定。她是被包办婚姻的。所以多年以来,许多她对性格的认知也成为了我的 一部分。因此我观察人们时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观察事物的方式。对我作为一个作家而言,这相当有用,因为讲述虚构故事的作家必须懂得人性中非常真实的东西, 必须观察人物以便知晓其根本,而并非仅仅是发生在现在或十年前的情况。它也可以发生在他们父母的过去,也可以是他们父母如何对待,如何克服,或没能按他们 的标准生活。检视别人的过去时,也给令我理解。我着迷于这些,有时我想说“不,不再写什么三代人之间的故事了”,但我认为我写作的部分理由与寻找自身的意 义有关。我写作是要取悦他人?那没有意义。我可以写那些令人愉悦的故事,但我花了生命的那么多年写作,我每天的想法应该有意义,因为那是我的生活。
您下一本小说的题目《惊奇谷》有什么出处?您写完了吗?
还没有,我希望我写完了⋯⋯ 只是他们想先要个题目。一方面,这题目与我去过的贵州的那个山谷有关,因为那儿太美了。你可以从每个角度去观看那儿的生活:是艰难而拮据的生活。然后我在 柏林看见了一幅山谷的画,它名叫《惊奇谷》。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后面是美丽的日落,或者,或许是日出。太阳穿过云层。非常平静。然后到了前景,画面变得 有些不祥而黯淡。山谷、树和河流以某种方式变得有点慑人。所以我看着这幅画的时候问自己“我是从那个美丽、平静的地方而来,还是往那儿去?”。我觉得在我 去过的那个东村,我也同样是个局外人。我把这些图景、问题同这场景结合起来。
那对您而言,总是先有书名?
不,书名通常最后才有。这一次,只是因为那幅油画的关系。我便用了那题目。我喜欢惊奇谷。从宗教的角度有好几种解读方式。一种是苏菲教的文本。那是好事。 是你感觉接近上帝的地方,你会在死之前感觉平静。而在一种基督教传统里,那是你失去生命中一切的地方,你的骄傲感,你的成就,所有的爱,一切的意义,你失 去一切。你对生命一无所知,对于要发生什么也没有想法。而那就是你将死时。多么可怕!两者都叫作“惊奇谷”。
那这本小说是否基于您的自身经历?
不,并不基于我自身的经历。但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基于一个问题,关于人物,或关于在特定环境下代代相传的问题。总会有一种变动。这是一个在我身体里的问题。所以背景设定如何几乎不重要。我总会选择一个我愿意身处其中的背景。我永远不会选一个工厂作背景,因为我不想在那儿。

您读过您小说的中译本吗?您觉得好的翻译需要有什么特质?
没有,我读不了中文。但我听见人们谈论。《喜福会》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台湾译本。另一个是大陆译本,简体版。数年前,我在上海见过译者程乃姗,并共进了晚餐。
一个好的翻译需要有叙事声音,有语调。有人告诉我我的意大利译本改变了语调,使之更加正式。而我总是想把故事讲得好像有人在对你说话一样。因此是不正式 的。是非常开放、诚实的叙事声音。不是那种假装的、或试图炫耀的、或者讽刺的、甚至单纯为了幽默的。《沉没之鱼》的叙事声音是母亲的。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 同的声音,但这依旧与我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这些问题有关。人们觉得这是个非常不同的故事但我只是在检视我熟悉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我作为作家的意图。人们读解,他们看文化符号或故事的意义。那并不是说这不是真的,而是说在几乎每一页上都有我每天做了什么的指涉。就好像一本日记。我打开书,说“对噢,那就是那天我所做的。”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只有我自己。
也许研究者们以后会发现?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发现。这些都在书里。是我自身的记忆。因为那也是我写作的重要性。那天我有那些想法,那些想法很快不见了,因为记忆力有限。但如果我将之写下来,它就是个记录,是我有过那个想法的证据。因此对我而言,这是写作的理由之一,也几乎是我拥有此生的理由。
您使用twitter或facebook吗?您相信社交工具或互联网会改变人们写作的方式吗?
我有过一个twitter但我随它去了。然后我有了facebook但我写得不多。但现在我发现我可以将facebook和twitter链接起来。所以 现在我那样做,并开始发布一些讯息。我觉得粉丝或朋友增长得如此快真是不可思议。我有5000个朋友的限制,有些人还在等待成为我的朋友。因此我创建了公 共页面。社交媒体很厉害,你发布一些东西,它会循环增长。开始很慢,但增长迅速。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影响力。
我认为社交工具或互联网改变了“谁”写作。人们有机会自我表达并被别人所听见。我不知道虚构作家是不是会写得不一样。非虚构作家会发现故事并非那么独家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写同样的状况。而有些写得不怎么好。
我认为虚构作家如今也有采用社交网络的形态,很多人会对同一个故事作出反应。像巨大的罗生门。一个5000人的罗生门,5000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故事。
人们也用它来做广告。我还没有机会说“噢这是我的新小说”。但事实上感恩节前后我会有个新短篇出版。是我新书的一部分。一个章节。有个新的杂志在寻找 10000词以上的短篇,我正好有那样一个章节。我在小说出版前不让别人读我的故事。我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我甚至不让我的丈夫读,只有我的编辑知道我如何 工作。但这一次我想,人们读到了又会怎样呢?这是个很幽默的段落,也不会透露书的其余内容。所以它会被出版。人们可以购买并下载。看看会发生什么会很有意 思。编辑说“这会改变人们看你的方式”。我开玩笑地叫这故事“性菜单”。短篇会发表在byliner.com。第一个在那儿发表作品的人是 John Krakauer。现在他们开始做小说了,我是第一个。
最近您读哪些当代作家?您读什么文学杂志吗?
我订阅了《纽约客》。还有《三分钱评论》(The Threepenny Review),一本非常文学的杂志。就像小小的报纸那样。但它的作者有西班牙作家 Javier Marías那样的,所以也很国际化。我也用iBooks和Kindle,也用iPad读书。一般我在这些工具上读书是为了做研究。
我刚刚拿到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新书《加拿大》的试读本。我很喜欢理查德·福特的书。从我开始写小说起,我就一直读他的作品。但我读这样的东西之后会感觉灰心。我还记得读南 非作家库切的《耻》之后,我想“我干嘛还要费心写作呢”因为那本书的叙事声音如此清晰,影响力如此巨大,在最后有种吞噬一切的力量。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遇 见了库切。我没有意识到他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有天晚上我以为我受邀去那儿做个演讲,但其实我需要讲一堂课。因此我只好迅速地想好在那一小时里要讲的东西并 接受提问。之后,写作项目的负责人朝我走来,说“我要把你介绍给库切先生”。我想“这就是那位卓越的作家啊,他听了我刚才所说的话”。我想他会觉得我所说 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但是他说了“我觉得你的话很有趣”诸如此类的话。那种表达法经常用在你没有什么好话要说的时候。但这一次,我听见写作系主任对我说 “不,那是真心的赞扬,因为——(1)他在这儿的日子里,从来不去大学的其它地方,不去其它课堂,不去社交聚会,而他却来了您的课;(2)他希望结识您。 那说明他是真诚的。他那样说并非仅仅为了礼貌。”于是我如释重负,感觉很荣幸。
那您觉得您和库切先生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他在新书《夏日时光》里同样书写了童年自身的经历。
在虚构作家身上我总是会发现某些东西。你可以批评他们总是一再写同样的东西,但我们的执念是如此特别,因此我们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复这些执念。他们的确在书写同样的执念,但不是在写同一件事。而那正式他们作为作家的身份。
您觉得好的写作有什么标准?
语言最重要。确切地说,不是第一。语言要和非常独特的叙事声音相结合。这声音必须是非常特定的。对我而言,在叙事声音里包含了一组对于世界如何运作的信 念。你必须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怎样发生的。因此在那叙事声音里,是一组哲学性的信念,一组科学的信念。从头至尾都要很清晰。不是那种人人都有的声音。 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你通向世界的指南。因此必须是一种聪明的声音。
我喜欢故事。我不喜欢那种不知所终的故事,非常缓慢、看起来世界不怎么变化的故事。当我打开一本书,读第一段,如果我不喜欢语言,我会把书关上,无法继 续。我担任过一些小说比赛的评委。我曾作为“最佳美国短篇小说”的客座编辑。那是一种荣誉,因为当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读过不少也学到不少写作的技巧。 就是从那儿开始我想到了关于自身写作的种种问题,什么是叙事声音,故事是怎样的,我对什么感兴趣。编辑“最佳美国短篇小说”时,我读了当年出版的最好的 20多部短篇。我觉得很不安,我何以来评判当年的最佳小说呢。但很快我意识到我是有标准的。最终我意识到,它就在第一段里。后来我担任了《洛杉矶时报》 “西刊”(West Magazine)的小说编辑。我们刊登新小说,其中一些来自新晋作家。又一次,我面前有一堆手稿。我会很快地读开头几段。随后我再读下去。有时我读到第 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然后我会知道是不是有陈词滥调,我以前时候听过那个故事,或者,他们是不是太过用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小说里是不是没有东西 感觉像真的,是不是试图讲述关于人性的某些东西。当然这毕竟也是很私人的。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真正的标准,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评委还是作家。
您对文学奖项有什么看法?您曾一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奖项每年都会变,因为评委变了。他们不是同一批人。奖项也不会办法给特别流行的作家。他们会找一些新的作家,或特别是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很政治的作家,书写 国家、或美国现状的作家。那也很自然。人们常常将文学视为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把文学看作文化和政治的代表。我认为有些作家在这点上做得好。但我不认 为那是文学的唯一功能。可以有政治小说,可以有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但那不是文学的必然使命。有人曾对我说,你的小说真的应该表达我们社会的伤痛,或不公 平,而我的回答是,那就应该是你写的小说,如果这是你生活的目的。文学的使命应该由作家来决定。正面的模范式写作让我发疯。那是宣传工具。
您是否阅读那些华裔美国作家的小说,比如李翊云或哈金?
是的,我读。哈金的短篇是美国最好的短篇之一。我也很喜欢李翊云。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韩邦庆写的学术研究书。他是1880至1890年代的作家,是个记者。他是最早创造出一种新闻报纸的人。他写的连载小说,后来由张爱玲译成了英文。
你会不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非虚构的书?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对小说更感兴趣。时不时我想我要写点东西。我想写一间屋子。我同父异母的姐姐觉得房子完全属于她。于是她把房子卖了,自己拿了钱,不告诉别人。我 们后来发现了这件事,但她有她的道理。我要把它写成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真实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她的性格如何?如果房子卖了我并不想要那些钱,我会说“你留 着那钱吧”,但在家庭成员之间,这样做很奇怪。但随着时间,一切变化了。我想:她的个性是否一直如此?或者反映了一种变化?在特定年代,人们对离国而去的 人有种潜在的不平等、或不公平的感觉。这让他们痛苦。他们想像在美国的人们有更容易的生活。我的一个姐姐被送往乡下,并在那儿生活了19年。她并不苦,但 其他姐妹们觉得她苦。所以你想到这些背景环境,想为什么在现在特定的时点上会做出那件事。他们会比谁受的苦更多。我理解了她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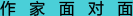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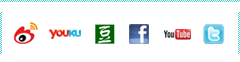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