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没有死
颜歌
在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这个号码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响起来。
有时候是厂里开会,爸爸正训着门市部那几个嘻哈打笑的女售货员,有时候是和外头的朋友们喝酒,五个人喝到第三瓶茅台,包房里烟熏火燎,有时候更加糟糕了,爸爸正在和女人们做爱,或许是妈妈,或许是别的倒生不熟的婆娘。总而言之,事情正到酣畅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听到这曲子,爸爸先自软了三分,等看到上面的名字确凿是“妈妈”,他便连送起腰杆的力气都没了,爸爸像鸡毛一样飘下来,捡起电话,对着话筒,暗暗清了清嗓子,走到走廊里去,叫了声“妈”。
奶奶就在电话的另一边,她扯着电话线,扯着爸爸的心颠颠,爸爸听见奶奶说“胜强啊”,爸爸就说“哎,哎,妈,你说”,他靠在墙壁上,离对面那面墙不过一米半远,离奶奶不过隔了三五条街,爸爸说:“妈,我知道了,你别管了,这事我知道了。”
爸爸挂了电话,重新走进房间去。几分钟罢了,世上的事情却都变了,女售货员咬着耳朵交换着女儿们的私情,朋友们发短信的发短信,点烟的点烟,床上的婆娘居然弓着背在扯脚后跟的一块茧皮,爸爸咳嗽了一声,反手关上门,还是要把没干完的事干完。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床上的婆娘恰好是妈妈,就免不了要谈两句奶奶的事情。
妈妈说:“你妈打电话来又什么事?”
爸爸走过去,脱了拖鞋翻上床,掀开铺盖往里钻,说:“哎呀,你不管嘛。”
他们就继续把没干完的事干完了。
过了一会儿或者稍久一些,爸爸走到走廊上,穿着暗红色的条纹衬衣,打电话给朱成,他说:“在哪儿?……嗯,来接我一下。”
他挂了电话走下楼去,走了半层楼又忽然停下来,爸爸实在想不过,站在楼梯里,屁眼鸡巴猪牛马,肠子下水君亲师,把这种脏话搅着骂出来了,“砍脑壳的!”爸爸说,“老子总有一天弄死你们!”“弄死你们龟儿子的!”—他从五楼骂下了一楼,从三楼骂下了一楼,站在平地上,抽了一根烟,远远地看见朱成开着黑漆漆的奥迪车过来了,他就把烟甩在地上踩得稀烂,打开后座一屁股钻进去,说:“去庆丰园。”
朱成便打转了方向盘,滴溜溜往西街外开,中途他们自然路过了十字路口,爸爸从车窗往外看,两条路上歪瓜裂枣地杵着人。从去年天美百货在这开业以后,马路上的交通秩序就每况愈下,比如有两个谈恋爱的小年轻,互相搂着腰不管不顾地从车前面穿过去,比如一个手上提满了东西的少妇,也没牵住自己的孩子,几乎就贴着车的后视镜冲过来了。朱成一个急刹车,差点撞到他们,便伸出去头问候他们的祖宗十八代。
“朱成,脾气不要这么躁嘛。”爸爸坐在后座上,说。
“薛厂,这些人就是欠骂,硬是觉得老子不敢撞他们啊!”朱成调着方向盘从人堆里钻了出去。
“现在年代不一样了嘛,穿鞋的就怕光脚的,开车的就怕走路的。”爸爸说。
“就是!”朱成应着,“中国人太没素质了!”
他们继续说了几句,就过了西街神仙桥口。大前年,这里新修了个公园,把原来残下的烂水沟填了个严严实实,爸爸从车窗里能看见公园里聚了好些老人,说话的说话,不说话的就干坐着,这些人里自然不会有奶奶,爸爸摸出手机看了看钟。
到了庆丰园门口,爸爸说:“朱成,不开进去了,你今天回去了嘛,晚上不用车了,等会我自己走回去。”
“我等你嘛,难得走。”朱成规规矩矩地说。
“两步路,我自己走一下。你就不把车开到厂头了,明天早上八点直接来接我。”爸爸交代完,开门下了车。
爷爷死了有两年了,去年春天,保姆唐三姐说她儿子喊她回去带孙儿,一转身就回了乡下,奶奶说从此再也找不到称心的人,罢了罢了,就一个人住着家里那套老房子,三室两厅,钟点工也不要,只想图个清静。
今年,奶奶比去年轻了,矮了一寸又一寸,这些爸爸都知道。他走上三楼,拿钥匙开了门,十次有八次都看不到奶奶,房间里堆着各种书、杂志和报纸,看起来像几个月都没住人了。“妈!”爸爸叫奶奶,“妈!”他又叫了一声,像是生怕奶奶就要这样没了声气。
“来了来了!”奶奶还是应了声,从里面随便哪间屋就出来了,“胜强,你来了啊。”奶奶说。
“来了啊。”爸爸一边跟奶奶说话,一边到阳台上,他在一盆兰草边找到了奶奶放在那的烟灰缸,把它握在手上拿进客厅,放在茶几上,点了一根烟,坐到了沙发上。
“又抽烟!又抽烟!”奶奶坐到藤椅上,看着爸爸直摇头。
“哎呀,你不管我嘛!”爸爸说。
“我不管你还是哪个管得到你。”奶奶轻巧地说。
“对对对。”爸爸抽口烟,应着奶奶。
“跟你商量个事。”奶奶说。
爸爸一边听奶奶的话,一边细心地观察着她的样子。奶奶老早就白了一头头发,但总是烫得一丝不苟,曲曲折折地贴在头顶上,穿着一件淡绿色的丝绵上衣,灰底白花的丝绵裙子差不多到膝盖,而在膝盖下面,肉色的短袜上面,奶奶把小腿露在外面,皮肤是灰白色的,至少有五六个秤砣坠在上头,把肉往下拉。
爸爸走了神,回想着第一次发现奶奶老了的具体时间。
那可能是在1996年,不然就是1995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奶奶忽然来了兴致,让爸爸带她去崇宁县的梨花沟看梨花。到了梨花沟,里里外外七八层人,奶奶坐在车里皱着眉毛看他们,那时候朱成刚刚来开车,做事还不太灵性,木鸡般黏在位子上,爸爸只有自己去扶奶奶下车,他牵着奶奶的左手让她下地来,顺手搭了把她的肩膀。
就是在那个时候奶奶老了,隔着衣服,爸爸能感觉到奶奶的皮都挂了在肩膀上,松垮垮地,简直要随着她的步子荡起来。他吓了一跳,差点没扶住奶奶,奶奶说:“胜强你让开啊,你挡到我我怎么走?”
爸爸退了一步,放开了奶奶,看着她往梨花沟走,爸爸说:“妈。”
奶奶停下来,回了个头,她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就和几分钟前一样,但爸爸居然不忍心看这张脸了。
“走嘛!”奶奶说。
他们去看了梨花,不是1996年,就是1995年。回平乐镇的时候,坐在车里,奶奶说:“你还是不要跟陈安琴离婚了,影响不好,人家都给你跪到了,你就算了嘛,两口子过日子啊少点计较,多点糊涂。”
“嗯。”爸爸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只觉得右手还是麻酥酥的。
“你听到没,胜强?”奶奶说完了话,过了半晌,还没见爸爸应她,就问他。
“嗯。我知道了。”爸爸重新说了一句,灭了烟,把眼睛从奶奶的小腿上移起来,看着她的脸对她点了点头。
“那你回去了嘛,我看会书就睡了。”奶奶交代道。
“好。你早点睡啊,妈。”爸爸四平八稳地答应了。
等到出了奶奶家,爸爸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却反身上了五楼。五楼往上再没有楼梯了,两扇门孤零零地对着,爸爸拿出手机来打电话,只响了一声电话就接起来了。
“开门。”爸爸说。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门便开了。门里俏生生立了一个钟馨郁,她应该是新做了头发,一头那么黑漆漆直溜溜地挂在尖脸边上,真是好看。
爸爸总算笑了一笑,走进去,把门关上了。
在爸爸的手机里,钟馨郁的名字倒老是变来变去的。有几个月她叫钟忠,后来又叫了半个月钟军,最近爸爸倒是返璞归真了,干脆把她存成了老钟。有一回,爸爸正在家里吃饭,电话放在饭桌上,忽然响了,爸爸倒还没马上反应过来,妈妈就瞄了一眼。“老钟的电话。”妈妈说。
“哦。”爸爸拿起电话,接起来,说,“老钟啊,正在屋头吃饭呢,打麻将啊?”
钟馨郁“啊”了一声。
“吃了饭都嘛,”爸爸笑着说,“今天我还要洗碗。”
他挂了电话,妈妈说:“老钟好久没约你打过牌了?”
“是嘛,”爸爸夹了一坨青椒茄子,扒了一口饭,“等会洗了碗我去应酬一下。”
“你吃了就去嘛,”妈妈乜斜他一眼,“知道你听到打麻将心都慌了,我洗碗就是了。”
爸爸就顺顺当当地出了门,觉得老钟这个名字的确是四两拨千斤,神来之笔。
晚些时候,钟馨郁问他:“我现在叫老钟了?”
“啊。”爸爸专注地摸着她的乳房,在爸爸摸过的乳房里,钟馨郁的乳房不算太大,但总是凉幽幽的,坠在手里像一块老玉。
“那你喊我一声呢?”钟馨郁笑嘻嘻地命令爸爸。
“老钟。”爸爸说。
“哎!小薛乖!”钟馨郁眉开眼笑地说,撅着屁股就把下半边往爸爸身上靠过来。
老实说,爸爸就欣赏钟馨郁这股没头没脑的傻劲,跟她做爱的时候,爸爸总喜欢张嘴就骂“你这个瓜婆娘!”—钟馨郁也不生气,便实至名归了。
爸爸和她搅在一起也有快两年了,说起来,这里面还有爷爷的功劳。
不过是爷爷死之前三个月的事,爸爸记得爷爷是满84上85,奶奶也都吃着78的饭了,正月里头,那天不过十五,不到早上八点,爸爸的手机响起来。
爸爸和妈妈都还在睡觉,铃声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爸爸迷迷糊糊地扯过电话,看到是奶奶,只得硬生生把火气都压了下去。“妈。”爸爸喊了一声。
奶奶在电话那边哭得悲悲戚戚,爸爸翻身来坐直了,问:“妈,什么事啊?”
“我要跟你爸离婚,我要跟你爸离婚!”奶奶悲悲戚戚地说。
爸爸和妈妈穿了衣服就往奶奶家赶,妈妈开着她的车载着爸爸,一边开,一边问:“你妈说要跟你爸离婚,有没搞错?”
一点没搞错。到了庆丰园,妈妈在楼下停着车,爸爸两步跳上楼去拿钥匙开门,奶奶在客厅里坐着,掩着脸哭。
“妈,妈,”爸爸走过去,看着奶奶,“你不要哭嘛,什么事好生说啊。”
“你问你爸!”奶奶空出右手来往阳台上一指。
爷爷在阳台上坐着一把藤椅,大冷天里春秋衣外头套了一件皮大衣,正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毛领子上全是烟灰。
“爸,怎么搞的啊?”爸爸走过去问爷爷。
爷爷摇摇头,不说话。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奶奶的声音从客厅传了过来。
爸爸哭也哭不出,笑也不敢笑,和爷爷两个难兄难弟般在阳台上互相换了一个眼神,爸爸说:“爸,你还可以啊,身体好嘛。”
爷爷倒是干笑了一声,妈妈从楼下蹬蹬走进来,奶奶像被谁踩了似的提高了哭声。
“妈。”妈妈叫了奶奶一声,也不知该进该退,望着阳台上的爸爸。
爸爸对她比了一个没事的手势,妈妈就往奶奶走过去了,她蹲下来,伸手扶着奶奶的肩膀,细声细气地说:“妈,你不要哭了,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嘛。”
“这日子没法过了,”奶奶说,“跟你爸说,我也给他当够了保姆,他爱跟哪个过就去跟哪个过,我也图个清静。”
那几天,保姆唐三姐倒是的确没有上班,回老家过年去了。于是妈妈张罗着热了昨天的鸡汤,下了半把挂面,又捞了一碟泡菜,一家人围着桌子好歹吃了早饭。
“胜强,等会给你姐打电话,把她喊回来,我今天就跟你爸这个人把这个婚离了,我一辈子清清白白,绝对不勉强人家,人就是要活个高兴,这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爷爷埋头吃面,一句话都没有,爸爸想说什么,妈妈扯了他一把。
奶奶总算没跟姑妈打电话,爸爸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三个月,爷爷犯了高血压,在平乐医院去了。直到最后那天,奶奶也打死都不出家门一步,无论是妈妈爸爸姑妈姑爹还是唐三姐,谁都没办法让她去看爷爷最后一面。
“不看!”奶奶说,“喊他另外那个婆娘去看她。”
爸爸思前想后,不得不坐在爷爷的床头,问爷爷:“爸,爸,你还有没啥要交代给我的?我一定帮你照顾。”
爷爷看了爸爸一眼,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他摇了摇头,握着爸爸的手去了。
英雄末路,爸爸悲从中来,想着爷爷这一辈子,忍回了眼泪忍不住气。他妈的。过了不到两个月,爸爸跟龙腾通信城卖手机的钟馨郁好了,就把她安顿在奶奶的楼上。龟儿子的这些瓜婆娘。爸爸说,“总有一天老子要弄死你们。”
没错,爸爸在做爱的时候是有很多怪话要骂。
说句良心话,爸爸也不是一个坏人。17岁生日过了才两个月,奶奶就安排他去豆瓣厂上班,带他的师傅叫做陈修良,陈修良也不是一个坏人,只不过就是有点懒又爱吃烟。每天爸爸从庆丰园出来走路去上班,路上都要给他买一包天下秀,陈修良拿了这包烟,就眉开眼笑地打发爸爸去做事,陈修良没拿到这包烟,就必定要骂两句鼻浓滴水的话,再打发爸爸去做事。
那一年在豆瓣厂,据妈妈说,爸爸做的事情是守晒场:5月份到了头,马上就6月了,苍蝇蚊雀都在天上飞起来了,打屁虫和土狗也开始在地面上横行—本来是一年里最杂花生树的时候,我们镇上的人却偏偏要去晒豆瓣—奶奶玉手一点,爸爸就被陈修良丢到了太阳坝里,磨皮擦痒地守起了晒场。
外地来的人肯定没见过平乐镇晒豆瓣的气势,爸爸倒是看得心都烦了。也就是横竖一坝子的土陶缸子,大半人高,两人合抱,里面汩汩地泡着4月里才发了毛的蚕豆和5月刚刚打碎的红海椒,以及八角、香叶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盐巴。那辣椒味道一天变两天地,慢慢在太阳下蒸得出了花发了亮,刚刚闻着也是香,后来也无非一股酸臭。有时候太阳大,晒得缸子里的砖红的豆瓣酱都翻滚起来,冒着打水泡,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拿了一根一人高一握粗的搅棍一缸一缸地去搅—搅豆瓣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陈修良为了教会爸爸这事没少给他吃爆栗子:“慢!慢!”陈修良在一旁叼着天下秀,做出双手下压的手势,斜着眉眼对爸爸吼。爸爸就慢下来,把手里的棍子调羹般在豆瓣里划着,陈修良却又不满意了:“现在快点!快快快!”他说。
棍子一搅,满缸的辣椒油就翻上来,混着水汽往爸爸脸上扑,呛得他连肠胃都红彤彤地,爸爸终于毛了,把棍子往缸子里一掼,对陈修良说:“到底是要快还是要慢!你逗老子啊!”
妈妈说:“你爸还以为陈修良要给他打上身了!”
但是没有,陈修良若有所思地吃完了烟,把烟头在地上按灭了,居然笑眯眯地走到豆瓣缸边上去,捡起棍子来给爸爸做示范。
“薛胜强,你看好:手要紧,腕要松,倒拐子要左右动,还有你要记好了,我只跟你说一次:你怎么干婆娘就要怎么搅豆瓣,懂不懂?这缸子豆瓣就是婆娘的屄,只要把婆娘干高兴了,这个豆瓣就搅对了。”—那一年爸爸还没有干过婆娘,他连光屁股婆娘长什么样都还整不实在,陈修良的话让他把目光死死锁在了他身上。
他看着陈修良在太阳坝下搅起豆瓣来了,用一种巫术般的节奏,慢,慢,快了,甩两腕子,又慢了。搅棍捣在豆瓣里,豆瓣发出水汩汩的呻吟,浸出红灿灿的辣椒油,冒着销魂的香气。爸爸就这样眯着眼睛在晒坝上硬了。
不用说,爸爸终于成了搅豆瓣的一把好手。他自认为在干婆娘这件事上也是的。
哦,还没说到爸爸怎么是一个好人的,但这件事可不像爸爸学会了搅豆瓣那么光彩。这也不是妈妈说的,但平乐镇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爸爸从来没有提过,甚至没有想过,但他肯定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自己想婆娘想得是发了愁的发了疯。
这都怪那个狗日的陈修良—爸爸汗涔涔地躺在凉席上,一边手淫一边在心里骂他,同时抽空想着镇上几个他觉得还漂亮的婆娘,想着她们光屁股的样子,等等等等。
但是爸爸还没失去理智,他从实际出发,抽丝剥茧地分析了眼下的情况,认为自己很难勾搭上一个婆娘,或者说,勾搭上一个婆娘又不被镇上的其他人或者奶奶发现—连续手淫了一个星期以后,爸爸决定到幺五一条街去找个货真价实的光屁股婆娘。
幺五一条街现在没有了,或者说它看起来消失了,只有知道暗号的人才能找到它的入口。总体来说,我们镇上所有的散眼子和二流子都熟悉它的位置,或者说只是全镇的人都做出了假装不知道的模样—实际上,出了西街往城外,接近三七二厂的方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街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桂花树,树上拉着绳子,时不时挂着几张毛巾和几件洗了的衣服,这就是著名的幺五一条街。爸爸还小的时候,行情是这样的:15块钱可以找个婆娘睡一次。2000年之后,也可能是2002年以后,爸爸又去了一次,那婆娘伸手就问他要150块,爸爸这才感到好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2000年,或者是2002年,就算是摸出150块吧,爸爸连屁都不会打一个。但是回到十多年前就不一样了,为了攒那15块钱,他真是绞尽脑汁,算尽了卿卿性命。
每天爸爸在家头吃早饭,然后去豆瓣厂上班,中午饭和晚饭都在厂里的食堂吃,除了每天给陈修良买烟的钱,还真拿不到别的零用钱了—不得已,爸爸只有在陈修良的烟钱上打主意:一包天下秀两块钱,一包白芙蓉只要一块,这样一天省下一块,过十五天就可以去幺五一条街。或者,有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一包天下秀两块钱,一包甲秀是四毛,一天省下一块六,过十天就可以去幺五一条街。
爸爸在半张纸上把这两种可能性反复算了三次,走在路上,掂量着那五天的日日夜夜,站在烟摊子门口,眼睛看着架子上的烟,脑子想着脑子里的婆娘,最后他心一黑,牙一咬,铤而走险,对老板说:“一包甲秀。”
陈修良倒是没多说什么,他把烟接过来,眯着眼睛瞄了一眼,“嘿!”了一声就算了。反正,吃烟也是吃烟,大热天里,他打着光膀子,坐在一棵大桉树下面,嘴里叼着半根甲秀,太阳明晃晃地,爸爸也不知道他看着哪里,他索性就不看陈修良了,埋着头搅他的豆瓣去了。
那豆瓣发泡的声音真差点狗日的要了他少年郎的小命。就算是现在,爸爸走过晒坝的时候都要忍不住多看一两眼那些豆瓣缸,就在一个坝子里,齐崭崭的全是初恋。
长话短说,爸爸麻着胆子给陈修良买了十天的甲秀,终于攒上了16元整。那一天,鸡公一叫东方白,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幺五一条街破了处。爸爸的记忆有点模糊了,他想不起来到底是因为那个婆娘特别有职业素养,或自己真是天生神功,他只觉得那天婆娘的叫声格外不一般。事毕,爸爸把兜里的钱都给了那婆娘。
“小兄弟,多了一块钱。”婆娘倒是好心,说。
“多的给你了。”爸爸轻描淡写地说。
“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从小,奶奶苦口婆心的教育总算没白费,爸爸遂成了个乐善好施的好人。
这天晚上,爸爸和高涛以及钟师忠两个在飘香会馆吃饭,不知道怎么的,就说了以前幺五一条街上的红幺妹—高涛抽下一口烟,把烟屁股在餐盘里剩下的半截鸭屁股上按灭了,用二指指着爸爸,醉醺醺地说:“老钟,你还记得到那个红幺妹不,就是薛胜强的那个初恋情人呢?”“龟儿子的初恋情人!”爸爸啐了他一口,他打死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就是被红幺妹破了处。“不管嘛,总之你娃一天到黑就朝西门外头跑嘛,为了跟红幺妹睡一觉,跑到黄家地头去偷人家兔儿,那次,你还记得到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爸爸和他的朋友们到了那个年纪,喝了一点酒就要开始忆当年的。“就是!我想起了!”钟师忠发话了,“对的!那次他把他妈气死血了,他还跑到我家头来住了两晚上,这个虾子!”
“你们两个老鬼儿子!哪百年的事了!找不到事说了啊?”爸爸抓起桌上的半包软中就朝钟师忠头上打,他笑嘻嘻地抬起手接了个正着,抖出了一支烟来就点燃了—包间里的女服务员捂着嘴偷偷地,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声。
“都说到这儿了,”钟师忠抽了两口烟,好歹摆正了脸,问爸爸,“老太太最近还好嘛?”
“精神得很!”爸爸说,“前天才把我喊回去给我交代要过八十大寿的事!”
“哎哟!”高涛拍了个手,“八十大寿是大事哦!胜强,你要好生给老太太操办一下哦!”
“操办嘛!操办!”爸爸夹了一块酱鸭子,咂在嘴里连骨带肉地吃了,“老太太说了,全家人都要喊回来,我姐啊,我哥啊,全部喊回来,还有镇上的亲戚朋友,弄热闹了,老子反正整巴适嘛,等到这些平时鬼影子都见不到的仙人些回来嘛!”
“哎呀,”高涛听出了爸爸的怨气,安慰他,“胜强,哪个喊你能干呢,又在老太太身边,多出点心力也是应该的。”
“能干!”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事,爸爸来了火,“能干个屁,还不是没法了,社会逼的……”他举起杯子来,桌上三个人碰了一碰,把白酒干了,“妈逼的!”
这倒是真的,不是骂人话,爸爸扪心自问,他这辈子没被幺五一条街的那些幺妹把脑浆给操出来,现在还能算有个出息,在平乐镇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全是靠奶奶逼出来的。
“黄金棍下出好人。”奶奶经常说。
“慈母多败儿啊。”爸爸还记得,这是奶奶拿起鸡毛掸子打他屁股的时候最爱说的话—爸爸肯定还记得,虽然他同样不会承认了,直到他都二十出头了,在跟妈妈耍朋友了,打麻将被奶奶逮到了,她还是能弄得爸爸巴巴适适地脱了裤子,穿着一条春秋裤趴在板凳上。
奶奶从来是个讲礼的人,做什么事都求个周到,从小到大,她就斯斯文文站在爸爸边上,一掸子一掸子往爸爸屁股上抽,鞭子打在春秋裤上,说大声不大声,说小声也不小声。她一边打,一边轻言细语地说:“胜强啊,你要听话啊,我们薛家就看你这一个娃娃了,不要怪我手狠,慈母多败儿啊。”
屁!从小到大,爸爸每次都在心头骂,“你怎么不打姐呢,你怎么不打哥呢。”
就这样骂了二十几年,爸爸也没敢真的骂出口,但他算是想清楚了,打从奶奶怀胎十月把他生出来,他就是来这个家头当受气包的。
“小妹,把酒开起嘛!”爸爸吼了一声,指了指那瓶还没开的茅台酒,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钱嘛,纸嘛,肉包子打狗嘛—用着薛家的钱,爸爸心里总是格外舒畅。
在爸爸的手机里,存着一个叫做“戴知明”的电话。说来烦人,明明不想看见这个名字,却偏偏因为戴字排得靠前了,他打开电话本翻电话,多而不少总要瞟到一眼。有时候他看到也就看到了,但有时候他看到就要发无名火,有一次,他差点就下手了,要把“戴知明”改成“知明”,让它狗日的从D开头变成Z开头,图个眼不见为净—但是他终于没有下手,要让他把“戴知明”存成“知明”,好像他和这个人的关系变得亲热了,他也就宁愿吃个亏,多看这白脸鸡儿的名字几眼算球了。
至于姑妈,爸爸倒是不敢像对大伯这么对她,他规规矩矩把她的名字存成了姐姐。每次要给姑妈打电话了,爸爸都规规矩矩地走到人少的地方—走廊上、阳台上—翻出姑妈的号码,打过去,响几声就接通了,姑妈接起电话来,清清淡淡地叫爸爸的名字:“胜强。”
从爸爸有记忆以来,姑妈都不说平乐镇上的话,而是说的普通话,就凭这一点,爸爸从来都尽量轻言细语地和姑妈说话—电话通了,姑妈的声音传出来,就跟在电视上听到的一样,她说:“胜强,家里有什么事啊?”
爸爸就收敛了他满肚子的怪话,端端正正地,跟向大队长汇报工作一样,说:“也没什么事,就下个月不是妈要过八十大寿了,她想把大家都喊回来给她过个生。”
“噢!对,”姑妈的声音听来有些惊讶,“我差点忘了,是的,的确也是应该回来了。那你把日子定下来,到时候我回来。”
“嗯。”爸爸答应着,也是姑妈了,如果是其他人,爸爸肯定要在心里骂几句怪话,想:“戴知明,老子定日子,定酒席,你带起嘴回来吃饭喝酒,老子把你打到了!”
“一切都好吧?”姑妈问,“安琴还好吗?行行最近怎么样?”
“都好,都好。”爸爸热络地应着。
“都好就好。”姑妈说。
姑妈这一问,堵住了爸爸嘴里的话。别人不知道,包括奶奶都不一定清楚,可是爸爸心里明明白白,没有姑妈,就没有他和妈妈的今天—劝住他不和妈妈离婚的人不是奶奶,而是姑妈。
那次真是破天荒了,姑妈主动给爸爸打了个电话,问他:“胜强,你是不是铁了心要跟安琴离婚?”
爸爸不说话,他前一天自然是口口声声答应了奶奶,可是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爸爸不说话,姑妈自然明白了,她叹了口气,开口接着说:“胜强,我知道出了这种事,你要离婚,谁也不好开口劝你,可是我这个媒人还是想着再和你说两句,姐说话,你还能听得进去吧?”
“姐,你说。”爸爸老老实实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眼睛直勾勾看着门厅尽头的防盗门。
“我和安琴啊,好歹做了两年同事,她是个好女孩子,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我也算是看着你们在一起了,真是不忍心你们就这样散了,所以今天姐帮她求个情,不知道你能听得进去吗?”姑妈说。
“姐,你说嘛。”爸爸还是看着防盗门,那天。
“姐也不说安琴对了,也不说安琴错了,姐只想跟你说,你要是和安琴离了婚,你要怎么办?行行怎么办?一个家不能没有女主人,你这个年纪,这个能力,要再找当然也简单,你能再找一个老婆,可是去哪里再给行行找个妈?你要找个年纪和你差不多大的,那肯定也是有过去的,问题一大堆,你要是找个比你小的,那怎么像话?姐知道你,你现在厂里生意做得好,人也吃得开,年轻女孩子多是多,但都是玩玩就算了,哪能带回家,你想想啊,胜强,那个家里,你还能找谁回去?”姑妈说话的语气让爸爸想到了他在电视上看见她的样子,她好像在对着提词机背这段台词。
爸爸看着防盗门,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姑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最后归结于“你还能找谁回去?”
爸爸找不到这问题的答案,和妈妈结婚那年找不出来,现在也找不出来,所以他安安心心和妈妈结了婚,一过就是十几年。
“我知道了,姐。”爸爸终于说。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爸爸挂了电话,妈妈就刚好用钥匙窸窸窣窣地开了防盗门走了进来,她提了一手的菜,期期艾艾地,也不太敢看爸爸,低着头往厨房里走。
“安琴。”爸爸叫住了妈妈。
“嗯?”这一声叫得妈妈浑身一抖,似乎被吓破了胆。她转过头来看着爸爸,多年了,爸爸知道妈妈徐娘半老,姿色犹存,一张白生生的鹅蛋脸上镶着一只精巧巧的鼻子,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晚上吃啥?”爸爸问,一边问,一边往沙发后面靠去,拿起遥控器就要开电视,好像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晚上。
—那个晚上过去了好多年,妈妈终于重振旗鼓,坐直了腰板,站定了大房的位子,从贼变成了捉贼的,就算如此,纵便这般,家总算还是家,窗明几净,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爸爸知道这一切都多亏了姑妈当年的那番话,爸爸差点就没说出嘴里的话来。
“妈还说了,把大哥和刘星辰他们都叫回来。”爸爸总算说出了口,他实在不能不说。
“妈这么说?”
“是啊,老太太一心就是想着要把家里人都叫回来,谁都不能少。”爸爸说,“她说,80岁了,要热热闹闹过个生。”
“我知道了,那你就早点定下日子告诉我,最好是周末,星辰和小赵平时上班都忙,点点平时要上幼儿园。”姑妈交代了家里人的行程。
“好,我明后天就定一下告诉你。”爸爸赶紧说,“姐,你如果为难,我可以跟妈说一下……”
“没事,”姑妈打断了他,“胜强,你别管这事了,一家人就一家人。”
朝夕相处了将近20年,爸爸当然知道姑妈的倔,他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准备挂了电话。
倒是姑妈问起了大伯:“知明呢?你给知明打电话了没?”
“我知道打。”爸爸说,“姐你就别管其他的事了。”
于是爸爸挂了电话,重新翻开电话本,第一页就能看见大伯的号码。爸爸看着它,看了几秒钟,几乎就要按下去了。
但是他终于没打。“现在时间不合适。”爸爸想,“明天打吧。”
他就在电话本上一路翻了下去,不远万里翻到了钟师忠的电话,然后他打过去:“喂,钟娃儿,出来吃饭嘛?”“正在吃?甩了筷子出来就是了嘛!屁话多!飘香!我请客,我喊朱成拿三瓶茅台来,今天喝高兴!”他知道钟师忠这个酒虫子一定抵抗不了这个邀请,他果然同意了,但是他提出要叫高涛。
“喊嘛喊嘛!”爸爸知道钟师忠卖的什么药,高涛盘算着让豆瓣厂把明年的广告都承包给他的广告公司,又是打电话又是来家里送礼,已经折腾了两个星期,钟师忠一向和高涛要好,自然要帮这个顺水人情。
“大家弟兄多久不见了,今天一起吃高兴!”爸爸在电话里说,虽然他清楚自己的心思:“鸡巴大个门面,还好意思说是广告公司,也好意思跟老子做生意!”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爸爸念叨着,这样走出了那一扇防盗门。
这天晚上,爸爸和高、钟两个人,喝到第三瓶茅台,正在椅子上喘着粗气,眼见着包间的女服务员越来越像哪个仙女,电话忽然就响起来了。
已经是将近晚上十一点,钟师忠吓了一跳,对爸爸说:“是不是嫂子喊你回去了?”
“她!”爸爸哼了一声,还是拿起电话。
电话上清清白白地显示着“老钟”两个字,爸爸瞟了钟师忠一眼,拿着电话走出了包房。他站在走廊上,把电话接起来,粗声粗气地问:“半夜三更,哪家死人了?”
这句话说出来,爸爸自己吓了一跳,他忽然怕是奶奶出了什么事,一肩膀靠在墙壁上,钟馨郁在电话那边说了什么,但都给他自己唬得没了声音。他想到奶奶一死,这一家子人不知道要怎么出乱子,自己又不知道要怎么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就吓破了胆。
还好,他定了定神,听电话那边说了话,并没有什么大事,无非是钟馨郁忽然在夜里发了痴,哭哭啼啼让他过去。
“在外面的嘛,喝酒的嘛,怎么来嘛。”爸爸轻言细语地哄着这个瓜婆娘,最近钟馨郁不知道被什么鬼迷住了心窍,有些不安分起来。
“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来!”电话那边的婆娘说。
“真的来不到啊,明天来,明天一起来我就来,好不好?”爸爸维持着温柔的声音,想着,钟馨郁毕竟还是太小了,动不动用什么“必须”,还“我不管”,简直不知道是被谁惯坏了。
“不嘛!我就要你今天过来!”钟馨郁居然丝毫不领爸爸的情分。
爸爸靠在墙壁上,看着对面的墙壁,仔细观察着墙纸上有一块卷起的边角。这个场景让爸爸觉得无比熟悉,这就是每次奶奶打电话给他的情况。
这么一想,爸爸不由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个小小的钟馨郁也敢骑在他头上撒泼了,那穿着一套紫红色的工作服在龙腾通讯城低头哈腰这个哥那个哥地招呼客人的小钟如今安在哉!
爸爸把火和浓痰一起卡在脖子里,正准备一口气撒出来,就听见钟馨郁说:“你不来我就下去敲你妈的门,你看嘛,我做得出来,我把她喊起来把我跟你的事都说给她听,我看她要怎么说!”
就跟要做爱却拉了个手刹般,爸爸一下子就蔫了,上了年纪,难免会有这样英雄气短的时候。
进了包间,自然免不了被高和钟两个人洗刷了一番,说:“家头扯警报了嘛!要回去灭火了嘛!”
爸爸只有搂着包房小姐的腰,大声地说:“走了走了,带我去埋单!”
小姐意思意思推了推爸爸的肩膀,说:“薛哥,高哥买了。”
虽在意料之中,爸爸还是客客气气地“哎呀”了一番,顺手在包房小姐腰上捏了几把,这位小姐穿着连裤的丝袜,弄得腰上鼓出了一坨肥肉,爸爸就把这坨肉捏在手里,心中竟是分外怜爱的。
趁着这股性子,爸爸披星戴月,奔赴庆丰园钟馨郁的床上和她云雨了一番—也只得如此,不然深更半夜,心头又一股无名火,实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得好。
因为喝多了酒,爸爸明显感到自己今天状态不佳,不过钟馨郁倒是哼哼唧唧叫得欢畅,爸爸说“小声点,大半夜了。”钟馨郁在他身下斜了他一眼,说:“怎,怎么,你是怕谁听见?”
爸爸遂狠狠地戳了钟馨郁两下,万般委屈在心头,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古来只有累垮的牛,不见犁坏的地,难道他薛胜强真是受气包的命,为了让老母亲睡个安稳觉,包个二奶都弄得这么卖命,古来圣贤皆寂寞,为谁辛苦为谁忙。
“等到天亮以后吧,”爸爸在最后一次和他的情妇钟馨郁做爱的时候想,“等到天亮以后把事情都解决了,给戴知明打个电话,安安心心给妈把八十大寿操办了,不折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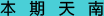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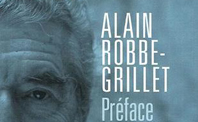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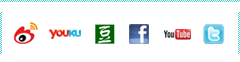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