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粉红野兽》封面
22日,星期一
兰波与一只暴君蜥蜴生活/睡在一起(稍后我会按顺序更详尽地解释),这动物就好像她一直琢磨的巫术/天使学中的猫。这只蜥蜴(它自然是赤裸身体的),在有些夜晚会在兰波的背部抓挠并噬咬出伤痕,留下风干后谜样的血色线条。
之后,在做爱的过程中,当高挑的她坐在我上面时,我的手掌会在她柔润至极却崎岖不平的背上游走。我嫉妒那只暴君蜥蜴,因为我知道,兰波在那小动物给予的友好又天真的疼痛中得到了快感与满足,随后我试着挑开她结下的痂,挑开这些血液的坚固线条,这些指甲刻下的痕迹:
“停,你弄疼我了。”
但是她喜欢这个,她要在疼痛之上累积疼痛,她觉得这样很好,央求我继续把结下的痂揭开、请求我抓挠那只小动物抓挠过的地方。正如阿尔托用小匕首在受伤的脑部搅动一样,她的痛苦焕然一新,她的兴奋更加兴奋,她的快感得到滋养。如此一来,我的功用仅限于延续一种男性的、平常的家庭工作,一种由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的野兽完成的近乎神话的工作(这种野兽是介于鬣蜥和波斯猫之间的东西)。
我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后继者。我抓挠它曾经抓挠过的地方,令崭新的血滴与生命得到释放,令女孩背上的印记与热辣的线条交错斑驳。如果我从后面强暴她,我会看到那只暴君蜥蜴完成的画作,那些于半梦半醒的夜间,在天真友好的游戏中留下的象形文字。兰波不能和她的小暴君蜥蜴做爱,但是她可以把自己耀眼如莲花般的胴体奉献出来,让那只小动物抓挠、轻咬、玩耍。
如果不与我睡,兰波会和那只小动物一起过夜,它会紧贴她如胚胎一般蜷曲的背部,像诡异至极的宫外孕,仿佛少女的背上长出了一只怪兽。如果我与她共枕而眠,便会像那只暴君蜥蜴(通常这种情况下,它已在垫上睡着,安静如一块被绣上的图案)一样贴在她身体上,轻噬着、抓挠着、用我的气息与方式愉悦着她的梦,直到察觉自己已经变成传说中的那个卑贱的/荣耀的动物。
早晨,在镜中,我看到了自己鬣蜥般的脸。
29日,星期一
兰波在吸食popper 时,会觉得自己的头像那些鼓鼓的气球,飘到了天花板,她的小脑袋仿佛极尽繁复的木刻吊顶,停留在那里,从她蓬乱黑发的阴影中迷茫地晃向天空的晦暗,而她的眼睛,她的被牛奶丛林里的色情狂扼住喉咙而窒息的聪明女孩的眼睛,会用眼白瞟一下天空,或用黑眸注视一下我,而此时的我正裹着大衣平躺着,读着科莱特 的作品全集,那恰是我送给这雌雄同体的少女的书。她那时喜欢科莱特。
“科莱特说,上茶的时候得洒出来一点儿,”她的脑袋从天花板发话了,“因为茶上得太好就像服务员了。这是不是棒极了?”
兰波拥有纤长的脖子,恰似一些支离破碎的、拼接粘合成的古典雕像的颈项,那些拼合点赋予了这些石雕一种瘦弱,而这瘦弱全然是现代的了,是古典世界做梦也无法想象的波德莱尔的现代美。
兰波拥有一对并不存在的乳房,正如那些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先锋派画家在完成裸体画时为了勾勒出胸部而绘出的两片空洞,我总期盼着在那两处浑圆洁净的空旷中看到进出飞翔的鸽子,但兰波却对街上凹凸有致的女人们羡慕不已。
“我要做激素治疗,我要做激素治疗。”她说着,俨然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用科学的渎神之罪来毁灭她阿多尼斯般俊美的自然样貌。
兰波拥有一双并不太小,却瘦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美丽的脚,她像那些Loewe的模特一样迈着步子,即便在穿着帆布篮球鞋时也是如此。她并不打篮球,也不做其它任何运动。兰波,在做爱的时候,仍然穿着她那双白色粗织女学生袜,那白袜一直延伸到纯洁无瑕、如神圣祭品般的膝盖那里。有那么一刻,在情欲的绝望中,我用一只空出的手(在多元的交合中,无论如何,必须力求一只手只满足一种需要)扯去一只袜子,让她的一条腿裸露出来,随后,用我的手指与她的脚趾五指相扣,她爱极了这个动作,就像她爱把我的龟头放到她的其中一只轻薄的、充满香气和听觉的耳朵那里一样。兰波就是这样。
兰波拥有一个竖直的肚脐,在那里,哈默尔恩的彩衣笛手 ——他毫无疑问是个作家——引领的老鼠都可以住下,就像生活在奶酪的孔洞中一样。兰波拥有的臀部如同天真的年轻星球一般,随着姿势的变换,它们会被奖赏/不会被奖赏。兰波拥有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两条大腿间的缝隙,那里会有三角形的、等腰三角形的、理论上的三角形的光束通过,此外还会有一片毛发的荆棘之地,还会有腿部内侧特有的一方细嫩的纯洁。兰波属于一种赤裸裸的幻透着苍白的黝黑,在她女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男孩、一段神话、一条雌雄同体的生命、一具雕塑、一位少年,还有一幅版画。
必须要暴力地占据所有这些,必须要在深入身体之时、到达高潮之刻的叫声中将它们合而为一。
30日,星期二
支气管炎集群。支气管炎是个集群。当我患病咳嗽时,就如同有人在用棍棒敲打一张承载历史的地毯:数千平庸的躯体,大量隐藏的我,从我身上剥离脱落,在12月的空气里踌躇迟疑。
健康时,我孤身一人。患支气管炎时,我是个群体。一个驻扎在我身体中、集结于我胸腔内的密集群体,一群蛀虫的乌合之众,一队混杂浑浊、衣衫褴褛的乱军,他们向周围散去,带给我伤口和羞怯。在一个人身体中扎营的支气管炎群体,就仿佛在支气管炎中扎营的无数杆菌。
它们只想喧嚷大叫,当我咳嗽得越猛烈时,它们就越能博得注意,就能钻到外面的世界,就能来去自如。我所有疲倦的我、黑暗的我、病态的我、胆小的我、平庸的我、愚钝的我、感冒的我,都在欢度支气管炎的节日,都在庆祝节日般的支气管炎。
如果我开始工作,咳嗽时,支气管炎群体就会如中世纪银河之路 上欢闹的朝圣者一般,将我的一切翻搅颠倒、在我的纸页上啐上唾液,把书页清晨的黄色(读者,你看不到这黄色,因为它不包含在书的售价里)用痰浸染成赭色/绿色。
之后,要考虑阴茎的问题。支气管炎群体的每一个个体都想有自己的阴茎,既然他们是我,当然像我一样,拥有这个权利。但我不能给他们每个个体都分配一个阴茎,也不能总共给所有个体一个或只给其中某个个体一个,因为,恰如之前所述,我的阴茎通常都在某个女孩的控制之中。
如果我出席一场高雅的午餐或晚宴,支气管炎群体会令我难堪,他们会冲盘子咳嗽,还会向邻座贵妇的美味佳肴吐痰。
“太不敢相信了,翁布拉尔, 您又带着那套红色革命理论回来了,” 星期三侯爵夫人说道。
看看,我该怎么向星期三侯爵夫人来解释,他们不是红色革命理论,而是支气管炎的国际联盟。
他们性欲难掩、呼之欲出,最终我起身离开,用红色围巾将之统统遮裹起来去拜访兰波,她通常就是那个,伴着美妙的金色之卵,在她那并不舒适的家中的舒适衣柜,将我的下体藏匿起来的人。
兰波,同往常一样,想谈一谈济慈甚至叶芝,想聊一聊她远方的家,或者讲一讲她刚编造出的暴君蜥蜴的故事,那家伙已经安然睡去,化作垫上的一块动物图案。然而支气管炎群体已急不可待,他们可不是来听故事的,他们只想大干一场,云雨一番。
他们和我不同,不是女人无限忠实的听众。
终于,兰波满怀爱意地看着我,将我的阳具从盒中取出,而300个支气管炎体,一个接一个地(我也算其中之一,当然,没有我的话它们什么都不算),满足着、款待着那女孩,使她呻吟、哭泣、哀求、叫嚷,在高潮的迷乱之际,令她再也辨析不清在那些支气管炎体和那些她认识的在巴黎的众多阿拉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庆祝着这性爱节日,它肮脏、强烈却又平庸。黎明已至,她,赤裸着,头上戴一条金属镉带,为我们每个支气管炎体送上雀巢巧克力奶,它们/我们还在睡梦中甜蜜地咳喘,而我们巴洛克式的灵魂早已沦为众多杆菌的盘中美餐。
- 1月 -
7日,星期三
翌日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兰波正用窗沿的积雪—乳酪样的白雪—来捏雪团,随后松手任它们自由落下,落入茫茫的工业基地深处,那些厂房拥有波浪形的带图案的屋顶,同样,也被白雪覆盖。
每个从她手中垂直降下的星球,都在坠落中带着天空平静安详的速度,划出这一日准确的维度,它们重重落下,在低处波浪形的雪中粉碎,在那片白色深处的漆黑阴郁中默默地留下意外的、黑色的爆炸声。兰波一直不断地制造着,凝视着这个处于城市后方的工业基地屋顶上的反向星空穹顶。只有从这里,从高处,我们才能在冬日的、偶然的美丽中看到这奇迹的发生,而那如旗帜一般的、连绵不绝的晦暗已在马德里上空广阔地铺展开来。
20日,星期二
这本日记我已写到了69页,(不知在书上会是第几页),我在写下这数字时所看到的是,男女上下相反的、用嘴满足对方的做爱姿势,它们的确非常相似。我的猫莱蒙托夫也会和那只斜视的波斯猫69,和那只它心爱的、它死板喑哑的、心爱着的猫用69的姿势做爱。但有时,它也和那只几个月的小黑猫这样欢愉一场。
那我和兰波的69呢?
兰波在她的不知羞耻之下充满了羞耻之意,她并不总想如此暴露在我的面前。也许她更希望是我,在她纤细身体的9之上,去作那个6。
但,当然,我们已尝试过了一切,现在可以开始思索柔顺的毛发了,它四处逃逸,如同烈火黑暗处的那些焰苗的末端一般(火的内部是黑色的,只有外表为黄色),它令下体的洞口更加温柔,令那些充满童趣、通向尾椎骨的必经之路更加细润。在一些夜晚,它会被唾液浸湿。
除此之外,兰波的爱,在我之前,在她自己之前,已是(如这世界上所有人的爱一般)比爱情试验更加繁复多样的爱,于是现在,她会在奄奄的喘息中,突然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
“咱们正在杀死对方,哥们儿。”
这娇弱的孩子,这年轻的病患,这黝黑的少女说我们正在杀死对方,而她自身的黝黑皮肤已然在最亲密的层面将她这黝黑的少女抛弃了,只丢给我一个因欲望或因缺乏维生素而苍白的她。我的心/老旧破烂的机器也许会对此表示赞同,但我没有这么说,因为爱情让四肢舒爽、令头脑清新、使思想更易地点,并重新生根发芽。做爱如此健康,健康到我惧怕告诉兰波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她可能会这样回应:
“爱要是这么健康卫生,我就不做了。”
女人们做爱的时候怀着毁灭情结(当然,她们读过文森特 )。但我好像已在日记本上翻过了这一页,或许该结束它并回到惯常的姿势了。

图说:弗朗西斯科·翁布拉尔
- 2月 -
1日,星期天
吗啡的瘾君子,赤裸的少女,光亮的乳房,还有在我们的时代被早熟的火花划过的美丽身体:兰波。
金色的历史,天使长的高潮,她毛发中的音乐篝火。西班牙大概就是那些英俊部长的丑陋阴谋、那些软弱政治家的艰难危机、那些教会阴暗的曼陀林演奏者、那些每40年都给我们带来一场刀光剑影音乐会的永久指挥(每世纪两场内战)、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高唱格列高里圣咏的投机倒把的高利贷商人,与之相伴的,是由于谎言而造成的信息、媒体、电力和电视的运转失常,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从光的神话中落至人间的卑微的小天使长,在热带甜蜜的柳木床上与我共枕而眠。
吗啡的瘾君子,赤裸的女人,轻薄的身体,恰如光芒中的一束光芒,被恒久的日复一日所穿透。在她的眼里、她轻浮的口中有一种能量,但那却是堕落的天使和屹立的女性的能量。生活披着周日的衣裳,毫不犹疑地给予我不断重复的、多样的、无用的、迟到的好处。在她遍布日渐茂密的丛林的外阴中,于她充满被束紧的希望的阴道里,我的手、我的阴茎、我的嘴,都是那只亵渎海洋的魔掌,是那只将睡着的鱼儿从海水的蓝色梦境之下掠走的魔掌。
凭着吗啡的翅膀以及正午时分的一双大腿,兰波,已经驱散/驱逐/驱除了守护天使和星期一天使(他之前已经降临,带着一个悲伤星期开始的预示),她自身意味着此时此刻的一个崭新、意外的胜利,而她的利刃也已将我人生平庸的永恒斩除得一干二净。
她,用一只铜样的手指,划遍了我的全身。
14日,星期六
我的充满新鲜橄榄油味道的、已被看透所有秘密的辨证的兰波,如同故事里被幽禁在浮岩塔中的公主,正站在那扇黄色大门后,有人向混杂了里奥哈红酒的她的泪河中扔去了钥匙,于是她将白粉切成了更细的粉末,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并不在乎利益得失不在乎爱情不在乎性不在乎印刷出的字句不在乎我不在乎他也不在乎其他人。而后,惊恐于自己空无一物的冷漠,她在出租车上吐了,待清理干净之后,她开始了一场长久的精神肉搏,对手是住在那扇大门的黄色里、拥有黄色肌肉线条的大力士,而培根的拳击手、站在分岔路口的一只耳朵在流血的梵高、刚从热带的午睡中被破碎的意识形态惊醒的高更,还有一个爱着她/爱着她的工会成员相继地出现在她面前。可可。
更好地说,是高乐高。
我厌恶工作场所的悲剧,(悲剧发生最自然的环境是诸神之间或希腊人之中,虽然苏格拉底从来就不喜欢古希腊戏剧。他有足够的理由。)我自身并没有吸烟却吸着烟,我在等待兰波的到来。而她姗姗来迟,将那扇黄色大门抛在身后,那扇门在拂晓散落的阳光里流出了鲜血,在腐坏的里奥哈红酒和年轻、诚实、辩证的爱情里流出了鲜血。
兰波在几个小时中将自己献给了我,岸边好客的鱼店仿佛也在她的黝黑的肤色中—这黝黑是属于我的—相继开门营业,而我们用疲倦的方式演练着永不疲倦的爱恋,直到她开始抽烟,直到她将宽大的毛衣从头上套下去,任凭它抚慰摩挲着她天使般阴部的第一片草木丛生的山丘,随后她将脑袋枕在我的肩上:“我爱你身体中蕴含的力量、我爱你与一切之间的遥远距离,我爱我所对你做出的一切,还有,请原谅我的坏脾气”,她对我说。在阿尔圭耶斯 的夜晚,在一处黑泉正为她孤寡的泉水哭泣时,我知道一扇黄色大门,如同培根的一个黄色拳击手,正等待着这女孩。在那里,向日葵是肌肉线条,而高更是一种沉闷的重量。孤独地,在自己的身上散着步,我是一家深沉的鱼店,有着闻起来像她的味道。
- 3月 -
6日,星期五
兰波坚持不懈地想杀死自己,她会去到梦的另一边,就像去到镜子或水的另一面。她钻进被子里,读一会儿书,给暴君蜥蜴留一些食物,一边听着柜子中和相片里古旧颜色的宾客们 通奸,一边甜蜜地自慰,最后,她服下一整瓶dormodor 。
一些时候她会去领略死亡,而另一些时候她会回到故乡。这些事她做起来自然至极。当身处家乡时,她仿佛已用阳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仿佛已成为伟大的躺卧者,成为被活埋的生命,成为没有坟墓的孤魂,在远处,她日复一日地过着一个因黄热病而死去的少女的生活,那少女的娃娃已将主人忘却,继续着每天的玩耍,而她的猫、狗,还有雕鸮,在她的死亡周围来去自如,仿佛那和一个越冬牧场没什么区别。
相反,在死亡时,兰波就好像已回到故乡。我从来没接受过她已死亡的想法,当她死去的时候,我也不曾感受到疼痛、惊恐、惋惜和枯瘦苍白的撕裂/撕碎。我相信她自己也辨别不清熔化在阳光里的家乡和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而墓地和广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她曾向我提及这种顺序/无序,之后我如那个沿海省份的鲨鱼一般,只感受了一星期她的陆续的、极其现实的、周期性的、决定性的死亡。死亡什么都不是,如果想成为一样东西,首先要变得像它:变得像一个沿海的小村庄。
兰波从死亡那里回来,带着诊所给予她的妆容,并保持了一段时间那种疲倦的高雅,那种死人想够到一本书或是想披上披肩时的疲倦的高雅。她的声音,当然,听起来就像她的一个姐姐的声音,在她出生前就在海中溺亡的姐姐的声音:
“下一次用手枪,药片什么的太没用了。”
这是她向生命问好的方式。
这不是凄楚阴郁的问好方式,绝对不是,她会选择一种时尚的自杀手段,并在这种行为的嘲讽/轻浮中,展现她与生命之间的新的和解。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死者已经生还,而此前在她来来回回、给她抛弃的衣橱贵客们送雀巢巧克力奶时,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点。(无需赘述,她现在对尼金斯基有特殊礼遇—因为她爱上了他:她总是爱上同性恋者,抱歉,只有我例外—,而不时从自己的食橱出来一趟的路易斯.卡罗的爱丽丝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则略受冷落,她从前喜欢被后者支配,然而这种事情已经不会再在夏天的衣橱中发生了。我想象着那个洁白的身体和那个黝黑的身体,那个成年英格兰雌马的身体和那个西班牙摩尔少女的身体,她们都在爱意的包围中被去年夏天带着新鲜香气的覆墙布爱抚摩挲着。大概就是这样吧。)
在她从死亡村庄归来后,我与兰波的第一次性交自然是充满死亡气息的,她湿漉漉的阴道渗透着坟墓上花朵汁水的味道,而那些落在她身上的吻则像极了墓园里的樱桃,她是加布列尔.米罗 (她衣橱中另一位常客)的迷恋者。
就这样,受益于她的自杀,当她的身体还含带着另外那个世界的烈火气息时,我尝到了强暴女尸的滋味。慢慢地,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正如春天从一片草丛跳到另一片草丛,将自己的游击战线不断推进,席卷向前),生命逐渐占据了这个死亡的孩童的身体。那是滋味混杂的日子,我口中的味道渐次从一个换到另一个,直到我重新拥有了全部的兰波。她已领略过了死亡,而我,已领略过了死亡的她。
因此,当死亡来临时,女孩,我闻起来将会有你的味道。
7日,星期六
粉红野兽。“粉红野兽”是那位业余小说家对女性的称呼,他是没有思想的思想家、研究文化的阿斯图里亚斯公子、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化公子、研究文化小姐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唐·佩雷斯·德·阿亚拉。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对他来说不是学识的渊潭,亲爱的兰波(我知道在你弥漫自慰气息的衣柜里没有隐藏类似的情欲/文学偶像)。拉丁语和希腊语,对这位先生来说,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积压于心的古老石块,是西绪福斯的巨石。
两块在他写作时、思考时、生活时予之以重压的巨石令他寝食难安、愚鲁笨拙、一败涂地。他在写给一位奥维多才子的信中提到,刚到马德里,他就染上了性病,从此便不得不秘密地将女士们拒之门外,而“粉红野兽”这雅致的侮辱也就由此诞生了。
他是一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双重野兽。
不好意思,给你上课了,亲爱的兰波,今天你本没有课的。我想说的是,粉红野兽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而是我们在交合中合而为一的整体,是那个拥有两个脊背的怪物,正如有人用更好方式、从与性无关的角度表述过的那样。你知道得很清楚(比我清楚),爱并不是必须面对面来做的,我们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性爱体位(这本书中就提到了一些,没有必要以图示之),但我相信我们始终会继续做那头粉红野兽,就像波德莱尔/让娜·杜瓦尔 、圣特雷莎和她的天使、纳博科夫和他的少女。从一对伴侣之中总会产生第三种感觉,不是他的,不是她的,也不是他们的感觉的总和,而是第三种东西。一对爱侣在交合之时,会诞生第三个生灵,那就是粉红野兽,一个一分为二的躯体,一个,如我之前所描述的,在你的镜中吃着白银牧草的人马。
这个将我们包含在内的生灵拥有两个躯体,还有第三个藏于那两者之间,它是四个乳房、两个脑袋、八个肢端的哺乳动物。我们,不再是你也不再是我。我们,是那头粉红色的野兽。
(唉,无论如何,她还是光亮明净的。)
15日,星期日
你的腋窝,亲爱的,是两处多余的阴部,也正因如此,她们永远出人意料、迷人异常。(我并不担心在这本爱的日记中重复叙述,也不在乎这个,我不知道是否已经说过现在正说的话。)我突然觉得,你的腋窝,和你黑暗而甜蜜的字体一样,是两片令人意外的阴影,是两口隐泉。
我想住在那里,住在人体关节的芬芳里,住在你身体轻巧的骨骼接合处,住在你毛发的发源地。一对天真无邪的私密之处,如同两个幽闭隐秘的幼女。在腋窝里,那两片我对之充满爱意的大陆,那藤本植物与阴影的世界,那女性的画卷,轻缓地徘徊眷恋。
在这本爱的日记里,在这叠日记体的爱意里,在这本书里,谈论、言说、书写,都是如此自由,只要是关于你的,文字便毫无束缚,比如当我们谈及你的身体,还有那黑暗的、女性的、温暖的腋下。
留下来在这里生活,成为那两抹晦暗、两片阴影的客人,她们如此细瘦,当你抬起手臂,用你带童年气息与尼古丁味道的手指梳理或揉乱毛发的时候,我便失控地爱上她们。
孩子,你是一本地理画册,是一张世界地图,而现在,我仿佛已在旅途中走到了你腋下充满爱意的岩洞。假如有人说过全部人类的历史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之中,我以为,更明智地讲,爱因斯坦和开普勒的宇宙中的全部山川河流星系尘埃都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就如报纸上说的那样,银河星系充满了女性气息,而那些美国人俄国人送到太空的不过是包皮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光影斑驳的腋下世界中,兰波,亲爱的,那里, 并不比我正在亲吻的你的腋窝更大一些。

27日,星期五
女孩,在今天,27日星期五,我眼前浮现出了你的名字,你的真正的名字,不是那个我送给你的、充满文学意味的、与你如此相配的名字,不是那个十分想变得像你的名字。
但是今天,亲爱的,就如我们从窗户探出头去的下雪的那天,你真正的名字,那个我知道、大家也都知道的、从来就存在的、寻常女性的平常名字在我眼前飘浮起来(Laforgue , 是的,你知道的)。那一刻世界充满的是向上飘升的雪花,是不合时宜的白色,是不符规律的美丽,是在你体肤之上航行的纯洁的延展,是偏航后遇见的岛屿,是水流冲刷的海中陆地,是溶解于澄明的一涓澄明。
我就这样看见了你的名字,在今天早晨,我就这样看见了身上写满你名字的你,从浅色的内心直至你黝色的边缘,那是你,那就是你。一个在你身体里下着雪的名字,一个在你身体里如落雪一般的名字,或者,是你,在你名字明亮的疆域里一直漫步。你真正的名字没有对你进行解读,它现在说着一个比你的黝黑皮肤更为黝黑的、关于你的真理。
事实会正好相反。
我送给你的、大家送给你的这个另外的名字,亲爱的,这个极其文学的、文学到可以因你蓬乱黑发中的绝望和你未写出的信中的字迹而唤你为兰波的名字,能对你做更多的解释。但这个名字却并不能最真实地解读你,它仿佛一件衣服,过度地概括着你,而你另外的那个两音节的名字,带着它之中不止一个的“a”,如窗户一样敞开着,直指你并不纯白的内心,直指你并不清晰的漆黑,它面对着你,看着你,看着最忠于自己的你。
今天我看见了你的名字,它飘到窗前,于是就下起了雪。
28日,星期六
兰波的双脚像另外的两只手,像到如描画出来的一般,如此完整、纤细、自由。如果她用脚来书写、绘画,或是做针线活儿,我能肯定,创造出的会是不同寻常的文辞手法,会是前所未见的美学风格,会是崭新、粗俗、独一无二的纺织技艺。有一次我曾对她说:
“你应该用脚去做卷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用右脚夹起一支笔,我也不相信她能做到,但用这种方式写出的字体,对教授来说,一定蕴含着迷人的气息:
“他们一定会因为吃惊而给你通过的。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手怎样活动,比如说在写信时会怎样地划过纸卷,但是除此之外,还应该去研究一下那些可以用脚写出的信件。”
那是走起路来一只总踩在另一只正前方的一双脚,它们交替落在那条穿越她生命森林的羊肠小径上,落在那条只有她才看得到的狭窄道路上。
“你迈起步子像模特一样。”
“滚蛋。”
当穿着极其雅致的高跟鞋时(配一条反差很大的破旧仔裤),她的双脚走起路来仿佛一对识路的鸽子。
当穿着平底凉鞋,只在两个赤裸的脚趾间有一条金色的细带时,她的双脚会留下希腊与罗马的印迹,而在那印迹之中,希腊与罗马只不过是街上那两团在风中被揉皱的报纸。
当穿着宽松的、红色和白色的学生袜时,她的双脚便充满稚气,当她踩在雪里,那双袜子会将她的瘦弱包裹在冰冷的雪靴中。我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她与我做爱时只穿着袜子,有些时候,并不用看,我就会扯下其中一只,然后用我的手和她的脚五指交缠。那就好像充满爱意地褪去幼女的衣装。
但大多数时候,她都会自然地光着脚。在晚餐时,在电影首映式,在那些明亮的夜晚,在穿靴子的冬日时光里,我能感受到,我知道,有两只光着的脚,仿佛两条赤裸的鱼,在我周围嬉戏玩耍。当她真的赤着脚在家中或街上行走时,你会看到,她脚踝间有金色的波浪此起彼伏。
- 4月 -
11日,星期六
你如此消瘦,兰波,消瘦到你的痛苦已逃离了你的身体,在房间中散步、呼吸、做体操,它们在你身体里憋闷了许久,几乎要喘不上气了。你如此消瘦,以至于你的身体里已没有地方能留给疼痛,因此,也许,自始至终都有一个疼痛为你戴上光环、对你阿谀奉承、紧随你的脚步、照亮你的容颜。
你如此消瘦,兰波,消瘦到快感也从你身体漫溢出来,在你的四周创造出笑声的花边、毛线缠绕的香槟,还有清醒的幸福,没有什么可以在你无形的身体里成形,你所拥有的、紧随你的、最盛大华丽的东西就是那些痛苦、快感、不安、高潮、愉悦、忧伤、惊喜、卫生巾、文件对你的追逐讨好,而这些东西本身在你那不存在的胸部和不存在的脊背之间是找寻不到容身之处的。你如此消瘦,消瘦到你身体里已没有地方能留给消瘦了。
你消瘦的消瘦, 兰波,就像海洋掀起的波浪,永无止息,因为在一层过后会有另一层更值得绘入画作的、凶猛的巨浪翻滚而出。你的消瘦仿佛阴影梦中的弯曲光线,又仿佛光线梦间的模糊阴影。在4月最初的迷乱思想中,光与影彼此靠近、相互融合,正如那些优秀的古典画作表现的一样。没有线条、没有方位、没有明暗,兰波,影与光渐渐迷失自己、茫然失措,她们就像两个相约来谈论自己孤苦生活的寡妇,而你就是那个坏女孩,误解她们、嘲讽她们:真可笑,这些老太太。
你就是那样,兰波,你就是那样,只有当你的灵魂如火上沸腾漫溢的牛奶那般生长时,只有当你的灵魂因安非他命、吗啡、莫扎特、new wave 和安眠药而膨胀时,你才拥有形体,因为你体内产生了如此众多的有形之物,多到似乎使你显得有了身体。我想是这样的。
你如此消瘦,兰波,消瘦到我的手不是在轻抚你的轮廓,而是在虚构、在编造、在想象你的轮廓,直到惊恐的触感从你小腹袭来,我才真正地碰到你,才让手慢慢地停下来,停在你腹部轻薄的存在中。
你如此消瘦,你的周围存在着一个臃肿的、浩瀚的、不断渗出汗液的世界。你如此消瘦,兰波,消瘦到你永远处于行将消失的边缘。
- 5月 -
15日,星期五
有一些夜晚会将兰波从我身旁偷走。我想说的是,黑夜会将兰波从我身旁偷走。
在白昼之间,漆黑阴郁的夜晚突然降临,她身着歌唱家的紧身衣、戴一顶布满星辰的礼帽,用电话和轿车施展诡计,将我的兰波带到了不知何处的地方。
不是男人把她偷走的,也不是毒品的黄色手掌、音乐的绿色魔鬼将她带走的。是一个夜晚把她夺走的,一个时而出现的黑夜盗贼,一个如海洋般、盛开在20个岩洞里的黑夜。
我不知道她会遇见怎样的女妖,不知道哪个瘾君子想去亲吻她的厌烦开出的黄色花朵,不知道她会喝些什么茶,会落入哪口井,然后在哪里睡去。
她早晨回来时失去了声音,他们从她身上偷走了声音,就像他们从另一些女孩身上偷走了贞洁一样,她需要很久才能找回它。
在我看见的那些夜晚—一些夜晚—到来前的黄昏,兰波仿佛被电话线铺开的网络缠绕起来,仿佛坠入她头发最黑处的阴谋,她徒劳地赤裸着身体,我似乎看见了清晨的汽车载着她开过去,看见了她黑色眼眸最浅处的黎明的纯白,看见了毒品的旗手,或者看见了她在自己鞋中的睡眠。
今天的是女妖之夜,昨天的,我不清楚是什么。
一个女妖之夜将兰波带走了,这个夜晚因男人而密实厚重,因女人而光彩耀目,被分享的虚假黄金因人们的年轻而一个挨一个地奖励着他们。黑夜的金属将梦境割裂,我的女孩清晨醒来时已被切破了脖颈。她找寻不到自己的声音,也止不住血流,那如玉兰花般残酷而美丽的伤口照耀着她暗紫色的嘴唇。有些白昼是虚假的黑夜。
兰波被扔到了充满日间嘈杂声响的内河港口,穿着肥大的破烂衣衫、带着被熄灭的光泽,她,是一个夜晚的遗迹残存。我坐下来一边读着西班牙银行年度报告,一边期待着女孩的声音,期待着它可以如黑暗玫瑰的梗茎般,痛苦地自下至上插回到她的咽喉,这样她才能再次谈起加尔西拉索 ,才能再次谈起报纸想讲给我们听的东西。
21日,星期四
兰波今天早晨是与一只黑粉相间的动物一同在床上醒来的(之前已有几次)。
“真可怕,太恶心了,丑死了,你看,它在这儿干什么?”
我走近她,把被单掀了起来。这女孩的身体总是处于黝黑或焦黑的阴影下。
和她身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阴暗的东西,那个会动的、长满毛发的、隐蔽的、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具有一种突兀的、抽象的特质。
“我倒是挺喜欢它的”,为了安抚她,我想这样说(事实上那东西也并不令我讨厌),但我知道这样只会让她更加疯狂,会令她的恐惧转化成愤怒,而她的愤怒会令她反过来针对我。我说过,这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你快做点儿什么,让它走,把它弄死,让它消失。它太让我恶心了,我恶心极了。”
“我们把它扔给暴君蜥蜴好么?”
她带着漫无边际的童真茫然地看着我:
“我的事你不要犹豫。”
好的,不犹豫。我坐在床边,向前倾着身体,仔细地观察。毫无疑问,那家伙有独立的生命,有一种陌生的直指南方的倾向,还有很多如纤细毛发的脚,也许是一个粉色的内脏,或者一只鱿鱼的肉瘤。
“嗯,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些什么。”
“快点儿,你总得说些什么。”
她瘫在床上,赤裸着身体,被单被掀翻在一旁,她仿佛是被雕刻而成的,仿佛一个破败坟墓上躺卧的雕塑,仿佛世纪初的一个死去女孩的廉价大理石像。这一切就好像一只蝇虫、一只惹人烦的蜘蛛、一只小动物或一个在逃亡却又静止的东西正在一位逝去少年的墓穴中筑巢。我清楚真相,但不会告诉她任何事情,如果我那么做了,兰波会惊恐抑郁地喊叫起来。
我只能爱抚着兰波的身体,好让她忘记那家伙,我只能深深地插入她的身体,好让那只蝾螈 怒火中烧、让三角形如蝙蝠的鸟儿带着尖厉的叫声归来。要将那只阴暗且片刻即逝的野兽耗得筋疲力尽,这样,我的女孩才能恢复平静与思考。
因为那东西,当然,只不过是她的阴部而已。

- 6月 -
23日,星期二
女孩/兰波拖着她装羽毛的箱子走了,拖着她装另外一种东西的(我不清楚是否说过那东西是什么)、却塞满了羽毛的箱子走了,那些羽毛有松鸦的、草原百灵的、雕鸮的、德里贝斯 的美丽苍鹰的,还有像猫一样的、聪明的、具有编辑气质的猫头鹰的(猫头鹰是长着喙的猫)。
女孩/兰波在一阵迁徙浪潮后走了,她说天空被鸟儿带去了别的地方,于是她期盼着在有海豚和鸟儿巢穴的南方城市,能捡到更多的羽毛,那是那些什么都不守护的天使(如果什么都不守护的话,他们也将不再是天使)在呼啸而过时丢弃的东西。
女孩/兰波为了鸟儿将我抛下了。她带着装羽毛的行李箱,头上系一条因发旧而从粉红色变成纯净藕荷色的发带。她必须跟随着鸟儿,在那下午的翅膀疲惫且顺从地落入城市时将它们收集起来:这是她对我说过的。在我的手指之间,轻薄地、微弱地留存着一种熟悉的母性气味。这气味/味道是女人的尼古丁。她阴部那柔软甜蜜亲切的尼古丁。
+ 原书《La bestia rosa》于1981年首次由西班牙巴塞罗那Tusquets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中文版根据1992版译出,以跳跃式节选涵盖了全书主要脉络,已获授权,轩乐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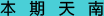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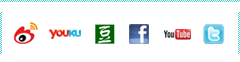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