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近900页的《2666》重如人生也轻如人生。2003年去世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在语言的雕琢上是个百年一遇的天才,而极度的敏感是他写作与生活的全部原因和借口。《2666》的故事格局并不宏伟,情节本身波澜不惊,悬念设置漫不经心且多半没有解答,然而,细节与情感却饱满到要溢出,波拉尼奥诗意绵延的句子好似决堤。
这是部无限忧伤的小说,来自一个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垂死之人。我们要谈到死亡,因为,《2666》与波拉尼奥此前的作品——如《荒野侦探》(The Savage Detectives)或者《遥远之星》(Distant Star)——区别在于情绪意欲逃离的对象。这对象,在波拉尼奥小说写作的第一个五年里,是内心不可抑制的极端与疯狂,在第二个五年里是内心本身的破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两难境地:波拉尼奥是个最容易又最不容易解读的作家。因为他的一切都裸露在句子里。在这样一部发挥空间巨大的长篇小说里,他没有试图设计博尔赫斯式的高智力迷宫,或者依赖捉摸不定的隐喻。《2666》由五个可各自独立成书的部分组成,五个故事之间的联系也只能用平淡无奇来形容——它们多多少少都与一个叫圣特丽莎的墨西哥小城有关。事实上,在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里,拒绝过度的情节交错、多视角叙事或者“互文”的设计感,反而需要一种只有少数作家才有的定力。这种类型的叙事往往会陷入诸如迈克.康宁汉姆(Michael Cunningham) 的《时时刻刻》(The Hours)那种套路。在《2666》里,波拉尼奥的宏大雄心与结构的关系,小于他对句子的迷恋。“波拉尼奥式”——假如我们要定义,是用延绵的句子和人生的细琐来填补刻意为之的巨大留白。五个故事里充满被拉长的长镜头特写,背景里的人与事和前景里的同样重要,同样被描写到极致却依然模糊。
整本书有一个让人无法抗拒想去寻找答案的秘密,那就是为什么它叫《2666》。在波拉尼奥此前的小说《符咒》(Amulet)里,这个答案在又不在。数字出现在这样一段话里:
格列罗路在夜里的这个时间,比起一条马路来说更像墓地,不是1974年或者
1968年的墓地,也不是1975年的,而更像是2666年的墓地,被遗忘的墓地,在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从未出生的孩子眼皮底下,浸泡在一只眼睛毫无感情的液体里,如此用力地试图遗忘一件事,却最终忘记了所有事。
可以说《2666》便是这样一种遗忘。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遗忘?波拉尼奥给你的是这样撕扯自身的句子,里面包含着异常强烈却又转瞬即逝的感情碎片。更令人信服的观点也许是,2666只是一个数字,一个与死亡一样让人不解的数字。“圣特丽莎大学好像一个忽然开始思考的墓地,却什么也想不出来。”
— 死亡如脱缰之马—
《2666》漂浮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如果说在波拉尼奥此前的小说里游离着生命终极的苍凉与无能,那么至少生命本身是可控的,无论失败的可能如何接近必然。但在这部最后的小说里,死亡好像脱缰之马,可见但不可控,遥远又可能随时奔到眼前。更何况,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匹死亡之马,而是多条互相交错的足迹。
波拉尼奥热衷于繁复甚至反复的细节堆砌,他习惯于把人物与故事宛如橡皮泥般掰开,以不同顺序排列。这种切分总是很随意,切成的并非一块块追求重逢的拼图,而是大小不等、软绵绵、具有粘连弹性与不确定性的物体,从一块里扯下一段,可以自然揉入另一块里,也可以自成一体。一排排用来分隔叙事段落的星号在波拉尼奥小说里非常重要,叙事于他而言,是一种不规则、不完整、从各个方向同时着手的堆砌,在最终的形状确定之前,没有人知道作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最终的形状本身也不能给你答案,除了这过程本身的虚无。每一个最终的形状都是死亡。
脱缰之马跑丢的地方总有另一匹马出现。小说的第四部分“关于谋杀的部分”独立成书也许更为妥当。这300多页的部分里堆满了死亡的细节:每一个被谋杀的女人死去时的穿着、死因(头颅骨折、胸膛穿破)、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如何被发现、是否有人认领、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如果有的话)、职业、男友、父母,等等。这部分的写法,是他另一部震撼文坛的长篇小说《荒野侦探》的再现,只是情节要残酷血腥得多。但波拉尼奥对死亡的残酷完全没有兴趣。如果死亡是2666,那么1993年到1997年发生的这一串连环谋杀案就像对虚无的冷静阐释。这个部分充斥的不是死亡的意义,而是死亡的无意义。
如果说《荒野侦探》里的寻找与探索只是人生,《2666》的第四部分,则是波拉尼奥对“侦探”这个他一直执迷的概念所做的最清晰的写作实验。波拉尼奥多次提起自己最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侦探。《2666》出版以前,也许很多人以为他的意思是文学上的,却不知道他的这个说法非常字面。在“关于谋杀的部分”里,对被杀女子案例的描述是警方笔录式的白描,总是以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成组成堆地一起出现。这些白描细节之丰腴,所花的笔墨之呕心沥血,有时持续几页之久。但被糅在其间的叙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关于谋杀的故事”里迂回的不是鬼魂,不是恐惧,而是像克劳斯.哈斯(被冤屈的连环谋杀案嫌犯)在监狱里说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所有人都知道谁是凶手,但没有人肯说一句话,甚至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有答案与没有答案,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甚至,知道答案比不知道更糟糕。
《2666》里有两种人物:被死亡之马拖在身后的,被死亡之马遗忘在茫茫之中的。在监狱里用自己的方式追逐真相的克劳斯.哈斯是后者,也可能因此更具有波拉尼奥式的悲剧性。这悲剧性是最终极的无能,跑得再快也无法追上的无能,波拉尼奥眼里拉丁美洲式的无能——“一个非常拉美的经验,就是永远在漫长而无助的等待当中,无论开始的时候还是结束的时候都无人理睬”。所以在整个故事里,最接近这起连环谋杀案真相的人出现在故事的最后,在私家侦探的调查过程当中毫不相关地患病死去,这丝毫也不让人惊讶。结局,在波拉尼奥的故事里总是最刻意地潦草。
奥斯卡·阿玛尔非塔诺是前者。《2666》的第二部分“关于阿玛尔非塔诺的部分”,是波拉尼奥与死亡的另一种搏斗。鬼魂出现了,灵魂出窍了,理智的散失是死亡的前奏,也是另一种生命早到的开始。阿玛尔非塔诺的死神是他自己,一匹脱缰之马将他拖在身后,俨然失控,但这失控是“幸福的”——“我要发疯了”,他想,“但我感觉很好”、“这些疯狂的想法……把混乱变成了秩序,虽然损失的是我们通常叫做理智的东西。”
阿玛尔非塔诺—圣特丽莎大学新来的教授,智利人,与这个城市里的连环谋杀案距离最远,与死亡的关系却最近。这个部分里,波拉尼奥得以糅入细腻与诗意。阿玛尔非塔诺的疯狂是圣特丽莎的疯狂,也是思想与文学的疯狂,或者疯狂的反面——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这是波拉尼奥在阿玛尔非塔诺身上画下的符咒。死亡是结束还是开始,或者只是一个逗号,甚至是极乐的逗号?
像波拉尼奥此前小说里的阿杜罗.贝拉诺一样,阿玛尔非塔诺是《2666》里的波拉尼奥,这点几乎毋庸置疑。阿玛尔非塔诺在帮助波拉尼奥面对死亡,面对“2666”。但这不是答案。就像波拉尼奥在这一部分里的符号学尝试,或者对杜尚的重塑,都是未完成的碎片,没有结论的实验。面对死亡,只有时间是武器。“关于阿玛尔非塔诺的部分”与之后的“关于命运的部分”有紧密的联系——第三部分的一开始就是死亡。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昆西·威廉姆斯(或者奥斯卡·“命运”,他的另一个名字)是波拉尼奥小说里甚少出现的北美人,北美黑人。母亲死去后,前往奔丧的“命运”进入了沉重的中年危机,他随后面临的是一次虚幻的圣特丽莎之旅。主人公名字里的隐喻一目了然,波拉尼奥用这个人物追逐结局。这个来自纽约黑人区哈莱姆的记者要去那里采访一场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的拳击比赛,整个部分里充满了他自我怀疑的内心活动—生命的虚无,身份的疏离,漂泊的迷惘,对“为什么我在这里”这个问题失败的破解反反复复,而更多的是一切之终极的无谓。“有用”——或者反义词“无用”,反复出现在这个章节,北美洲的实用主义在墨西哥的荒谬里变得难以吞咽,直到“命运”遇到了阿玛尔非塔诺的女儿罗萨——“命运”必须从被死神缠绕的阿玛尔非塔诺与圣特丽莎那里拯救她,也拯救自己。
在波拉尼奥的小说里,永恒的主题除了宿命论的苍凉,还有无法制服命运的悔恨,这两者的关系也是阿玛尔非塔诺与“命运”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像孪生儿女一样共存,互相撕扯。“命运”的悔恨在罗萨身上得到了短暂的化解,他们在越过美墨边境的时候,逃避的不是圣特丽莎的连环杀手,而是罗萨父亲奥斯卡·阿玛尔非塔诺的死亡。

—所有的虚无都能被填满—
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说《2666》是本“腐败”的小说—不完整、不清晰、自我毁坏意义上的腐败,“但它的腐败也是它的救赎,因为一本工整的小说,满是信号却没有噪音,则不是本真正意义上的书。”但格罗斯曼只说对了一半,《2666》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是本工整的小说,它的噪音是它的信号,它的不完整是它的全部。生命里充满的不是信号也不是噪音,而是种模棱两可、半静半动、无法定义的状态——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一种伤感的状态。一种命运从开端便指向空洞的伤感。
但《266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部腐败的小说——格罗斯曼说对的那一半。“厌倦沙漠里的恐怖绿洲”——波拉尼奥选择了波德莱尔的诗句为《2666》点题。波拉尼奥的噪音或者偏执般的细节,仿佛这厌倦沙漠里的沙尘,而真正的恐怖总是想象当中的。这种腐败感——《2666》对恐怖本身的漠然,对血腥或者残酷在字面上的逃避,对道德感或者人格完整的无视—甚至存在于最赤裸裸的死亡描写里。在连环谋杀案的部分里,最平静的是一个个接连死去的女性,即使描述得再细致,仍然是一具具没有下文的尸体。绿洲里的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克劳斯.哈斯的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每一个人身上的腐败感、虚弱感都超过了其它体味。
波拉尼奥习惯于大量的留白,每一个故事都不讲完整,尤其是激情澎湃的高潮过后,结尾通常是刻意的草草了之,数不胜数的短篇小说以“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结尾——格罗斯曼眼里的腐败与不完整。这是种相当残酷的写作方法,只有对虚无充满信仰的作家才能做到。而在这虚无降临之前,波拉尼奥却毫无保留地用无穷无尽的细枝末节填满视野。这种收放跌宕的手法,令波拉尼奥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
《2666》一开始,“关于评论家们的部分”像《荒野侦探》一样充满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各种思想纠缠,堆砌着各种人名、地名与不存在的文学流派和思潮。三男一女,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学评论家,对同一个神秘作家的热爱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在对这个神秘作家展开侦探工作的同时,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微妙的变化。这部分的叙事异常沉静,没有感情,但很快你会发现,这故事的关键既不是他们寻找这位名叫贝诺.冯.阿尔吉姆博帝的神秘作家的旅途,也不是他们之间徘徊的爱情,而是他们各自无限的孤独。大段的描写叙述的是他们等待的过程,无论是等待阿尔吉姆博帝的行踪,等待下一个见面的机会,等待不知何时会收到的电子邮件,还是三个男评论家等待女评论家利兹·诺顿对伴侣的选择。他们在等待“结局”的过程当中思考文学、梦见性,讨论文学、思考性。
《2666》的第一个部分,与呼应它的最后一个部分“关于阿尔吉姆博帝的部分”,比起中间的三个部分平实得多,甚至有种福楼拜感,执著于现代派叙事的流畅性和对人物的勾勒。如果说《2666》中间的三个部分更后现代、碎片式、情绪化,那一头一尾的两个故事则是另一种诗意,一种填补孤独的悠长。事实上,无论是这四个评论家,还是他们在寻找的阿尔吉姆博帝,都不像中间的那两个奥斯卡或者克劳斯.哈斯一样具有伤痕感。他们活在厌倦的沙漠里,也因此离虚无更近——那是死亡的一面。“只有在诺顿死去以后,我,或者说我们才能找到真爱”,同时爱慕诺顿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讨论他们的感情关系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诺顿在三个男人当中最终选择了年迈体衰与轮椅相伴的莫里尼,但这不重要,就像他们与阿尔吉姆博帝在圣特丽莎擦肩而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虚无中等待本身的绝望,或者希望,或者虚无。
用什么去填满死亡的空洞,《2666》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如何在五个从无到无的故事里铺张900页纸,波拉尼奥是个延长叙事时间的作家。他从不讳言自己对碎片感的沉溺,即使他习惯于把人物的人生经历以急骤的速度从头讲到尾,这种完整感也永远是虚无的。被加快几千倍的人生并非浮光掠影在自然播放,它们总会不经意地停在一个看似不重要的时间点,一旦停下,波拉尼奥会以慢动作延缓时间的步伐。一个巨大的特写,是利兹·诺顿任意一个孤独夜晚的所有思绪,漫长而不知所谓;是阿玛尔非塔诺的古怪哲学图表,箭头从托马斯·摩尔插入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利斯之间,封闭而神经质的臆想。波拉尼奥执著于以传记式的方式描写他全部人物的人生,包括那些对叙事线条而言最无关紧要的人。事实上,读《2666》需要耐心与韧性,需要对厌倦和虚无的全盘承受。
“关于阿尔吉姆博帝的部分”无疑是未完成的。这个最后的部分在语言上未到达波拉尼奥标准的精致,阿尔吉姆博帝这个人物也是个没有照过镜子的影子,只有轮廓没有存在感,活着却没有生活——一个德国人,“普鲁士人”。波拉尼奥小说里的德国人与拉丁人有着本质区别。德国人,无论是克劳斯·哈斯还是原名汉斯·里尔特的阿尔吉姆博帝都是诗人的反面,执著于破解宿命论的符咒,虽然通常无功而返。《2666》在这一部分结束是种遗憾,但这留白未尝不是对虚无的终极阐释。“2666”是死亡,它也是个盈余的数字,太大,太富裕。人生巨大的空洞,波拉尼奥用诗意的琐碎填满。执念于故事的亏缺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诗人,过眼云烟又积重难返的忧郁情绪是从生到死之间的一切。

图说: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如果还有力气,我会哭”—
波拉尼奥用句子征服了所有人,这不是句随便的评语。必须承认,作为诗人的波拉尼奥远逊于作为小说家的波拉尼奥。这个人的一切在延绵的长句里,诗歌对断裂与形式的追求对他是种束缚,正因为如此,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尝试诗歌,不断追求这达不到的彼岸。小说家波拉尼奥对自己也许永远是失望的,他与卡夫卡的相似度一定是被高估了,因为小说家波拉尼奥是不在乎克制与内敛的(诗人波拉尼奥正好相反)。与博尔赫斯的对比更有趣。波拉尼奥本质上是热爱博尔赫斯的,虽然两人在写作上的自然走向俨然不同,他们都对不可知与神秘有着本能的敏感,都是宿命论的儿子,但博尔赫斯的写作从现实抽离出去,而波拉尼奥则被现实浸泡。波拉尼奥曾经重写了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结果很明显——波拉尼奥的故事要长得多,细致得多,现实主义得多。
2003年的《2666》与1998年的《荒野侦探》相比,波拉尼奥叙事里的蓬勃激情略微减弱,控制与张力增加了。波拉尼奥从1993年开始从诗歌游弋到小说,2003年在几乎完成《2666》时去世,这期间在写作上经历过一个转折。第一个五年的作品几乎都与诗歌、诗人与拉丁美洲政治有关。波拉尼奥写作小说的岁月大多在欧洲度过,以至于《荒野侦探》、《符咒》、《遥远之星》、《智利之夜》(By Night in Chile)好像是对拉美大陆带有想象成分的回忆录。第一个五年的作品里,波拉尼奥最让人惊艳的是叙事节奏之激烈,一种绷在弦上的紧张感,恨不得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哪怕十天十夜不合眼也在所不辞,无论是情绪还是故事都浓得让人喘不过气。第二个五年的作品里,叙事速度明显有所放慢。波拉尼奥回到了第一本散文体小说《安特沃普》(Antwerp)里的虚无与剪影,但他对故事推进收放之迂回的把握能力却逐渐完美。《荒野侦探》里多少有些不必要的、偏执于细节感的堆砌与重复,在《2666》里仍有遗迹,节奏的张弛却更有诗意。故事的各种枝节更彻底地从主轴游离出来,回归却更不遗余力;故事讲得更悠长,但没有任何节点会让读者丧失注意力。短段落——有些只有一个字,“救命”——像言语之间长叹的那口气一样穿插在长叙事里。
一个将死之人,对写作的态度是松弛的。《2666》是本纯粹的小说,比起装满文学野心的《荒野侦探》、政治观念充沛的《美洲纳粹文学》(Nazi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s),《2666》呈现的是疲态的美学。这个人的一辈子等待的就是这个结局,阿杜罗.贝拉诺经历了皮诺切的智利,引领过墨西哥城的诗歌复兴,蜷缩过巴黎的穷人区,流浪过欧洲的各个角落,见证过《2666》的原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小城里的连环谋杀案,早来的死亡于他是宿命的必然,任何其它可能性都不够彻底。他也爱上过无数女人,梦见过很多鬼魂,吞咽过各种失败,才写出了与这个时代的气质所背离的伟大文学。编者后记里说,波拉尼奥在手稿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做完了,我活够了,如果还有力气,我会哭。我与你们告别。”
《2666》饱满、强烈又空洞、破碎。这告别留下了最大的空白,无法被阐释,更不用说被过度阐释。这个智利人,注定会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虽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句子里,像影子一样恍惚。按照美国作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的说法,《2666》像一个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小说里写到过的永生机,让所有的人物和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在这部小说机器里得到永生。
+ 2666, Roberto Bolaño, 2004; English translation by Natasha Wimmer, Picador, 2008.
+ 《2666》,罗贝托·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即将于2011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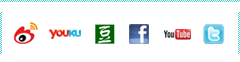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