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2010年,慕容雪村卧底传销团伙内部23天,写出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
慕容雪村没去悉尼,去了江西上饶
慕容雪村打入传销团伙内部之前,正准备去悉尼当访问学者。
他已经走过中国当代“民间作家”所能经历的一切:1990年代赶上网络文学热潮,出版《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晋升为畅销书作家;后出版更严肃的《原谅我红尘颠倒》,《多数人死于贪婪》等作品。他越严肃,读者就越不喜欢他,同行就越尊重他。中国作家协会向他伸出手,他选择留在民间。当他开始用文字谋生的时候,绝不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职业经理人生涯让他积累了财富,他的书总计也卖掉了百万册。他还具有中国作家稀有的天赋——入世感:照相机般的记忆力;聪明的头脑;华丽的文风,人们通常用“绚丽夺目”这个词形容那种阅读体验;能够承受艰苦劳动的耐力;洞察生活的虚假,多愁善感和荒谬的眼睛;他具备讽刺才能,又有真实的喜剧感和丰富的同情心,有时候,能感觉到他喜爱自己所讽刺的对象。他的样子也很适合当一个以文字做武器的“便衣侦探”:他的长相太普通了,叫人过目即忘,因此他隐入人群,就可以变成他笔下的任何人——公司老板,律师,骗子,或者传销团伙成员。
一个月以后,慕容雪村没去悉尼,去了江西上饶,加入一个传销团伙,还写了封遗书给弟弟:
“志安: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死了。如果遗体找不到,不必费心去找。如果找到,一火烧化,挖坑埋掉即可,身后事务必从简,不起墓,不造坟,不立碑,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有人联系你要写我的生平,不要答应他,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我的死不是大事,不必惊动世人……”
在传销团伙混了两个月后,慕容雪村写下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遗书收录在第一章。听说的人无不感慨其勇气,这种感慨出于赞扬:有参与精神与实证意识的中国专职作家实在太稀少了;这感慨又是一种错位的赞扬:评判作家的是他的智力产品,而非生产的过程。
“一个月后,我向警方报案端掉了这个传销团伙,很多人都说我勇敢,还有许多过奖之辞:为民除害,冒死潜伏什么的。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动机没有那么高尚,只是好奇心发作,想看看一天三五毛能吃些什么。”慕容雪村说。
再见到慕容雪村是在作协大楼。位于北京二环边的一个深宅大院,进门玄关处有浮雕“八荣八耻”,楼内的大理石装饰寓意着作协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慕容雪村第一次到作协,参加的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在5楼。据说10楼有一间更加宏伟的会议室,座位排次的变动隐喻着作家命运起伏,甚至引申出一门学问“10楼会议学”。
2010年10月,《人民文学》发起了“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非虚构写作项目,提供各1万元资助经费,支持非虚构作品。研讨会做为启动仪式的一部分,与会作家围坐,宣读早有准备的讲稿。其中语录有:非虚构是解释世界,虚构是描述世界。非虚构盛行来自想象力的绝望,你虚构得过现实吗,你虚构得过网络吗?非虚构就一定是真的吗,司马迁当年就特疑惑。非虚构在于情感的真实,在于作家个性。报告文学不如非虚构写作好听,干吗动不动就报告呢?
《人民文学》主编、非虚构写作项目的发起人李敬泽,是这项行动的旗手,对于为什么此时提“非虚构写作”,他有如下观点: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很多作者也不知道,那也不要紧,先做起来,树一杆杏黄旗,招降纳叛,做着做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就出于纠结的位置。文学像个幽灵,似乎不在了,好像在房间里看不到它,可又常常为看不到它而恼火,纠结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情绪。如果文学商业化,人们会说文学失去了坚守;如果不对商业化做出应对,那文学就在浪潮中退却了。左右不是,动辄得咎,没有人对文学感到满意。对文学,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读者也出了问题。新时代的读者,是最难对付的读者,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无所信。对世界的预设是从‘不信’开始的。面对一帮‘不信’的读者,要了命。”
“中国文学的非虚构精神,可以追溯到夏衍的《包身工》,到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大规模复兴。报告文学在发育不充分社会中,承担着过大的功能和职责——几乎是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是舆论发表平台。报告文学作者背靠公认的强大的真理,指点江山。而在‘不信’的时代,一个人摆出真理在握的样子,一个拥有巨大真理权的人批发真实,怎么会获得读者的欢迎?”
“同时,我们处于国泰民安的时代,中国现代以来从没有过长达30年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家成为专业化分工下的一份职业,作家的行动力减低,与世界建立积极联系的能力缺乏,很多作家靠二手材料写作。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
“因此,倡导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争夺对真实的发布权,发表权!”
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梁泓的《中国在梁庄》,潇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中,作为项目启动的先锋。三个作家也在座。与其他相比,慕容雪村没准备讲稿,他讲得不够宏大,显得不太会说话;而听到关于写作探讨的希望,也落空。这是个领导箴言录式的研讨会,有着领导的典型特征——先提目标,怎么实现,暂且不论。
2010年底,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新浪的年度好书榜”。这本书被称赞为:“作者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通过此书,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有不同的际遇——与对他行为的过分赞誉相对,这部非虚构作品面临着更严厉的审查。拖延良久,在2010年年末总算出版。慕容雪村在北京后海边邀了几位朋友,算做小型新书发布会,面对结冰的湖面,他朗读了被删节的段落:
“原来谎言真有无穷的魔力,只要坚持说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再坚强的人也会动摇,再荒谬的事也会变成真理,不仅能骗倒别人,连自己都会信以为真……”
“新新闻”主义
出生于美国喧嚣的1930年代,一直游荡在文学界边缘,当过报社记者和杂志社讽刺小说作家,在他真的写出一部小说之前,他已经是一位拥有大量读者的名人了。他是个有才能的表演者,一个自己作品的解释人,穿着标志性的白西服,看上去有点像花花公子,这套西服跟他的嘲讽智慧同样闪烁着光芒。他常常受到攻击,却从不显露自己的创伤,而对别人的轻慢和妒忌,倒是很敏感,并且,他并不总是相信自己会流芳百世。
他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一词并非由他第一个提出,据说出现于1887年,英国学者马休.阿诺德在一篇文章中斥责小报对英国文化的损害,而“新新闻”则能干,新颖,灵活,敏锐,富于同情心且无所不容,它唯一的缺点是华而不实。随后在这篇文章中,学者又用同样的辞汇形容了“民主”。汤姆.沃尔夫1972年在《纽约》杂志上重新阐释了“新新闻”,它对应的是旧新闻——以快速和传递信息为目的的新闻报道,同时属于“非虚构写作”的变称。
汤姆.沃尔夫在为“新新闻”选集所写的序里,列出四项“新新闻”借用小说的技法:(一)事件始末通过情节而非概要说明来呈现;(二)以对话代替叙述;(三)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视角,而非旁观者视角来陈述事件;(四)和写实小说一样结合诸如人物外貌,服饰,私人财物,肢体语言等细节描写,点明人物的社会阶层,个性,地位和社会环境。
汤姆.沃尔夫的浮夸风格一开始就获得了恶作剧般的成功。他的成名作,发表于美国版《Esquire》的“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是一篇长达49页的意识流备忘录;另一篇关于纽约格林威治村女子监狱的报道,开头使用了40个“啊——”,描摹女子监狱的女囚朝着窗外大吼调戏过路小伙子的场景。“新新闻”运动的参与人还包括诺曼.梅勒,盖.特立斯,亨特.汤普森等,受其影响,1968年杜鲁门.卡波特创作了了日后被奉“非虚构写作”典范的《冷血》。由于他们中大部分都精于表现,擅长塑造自我形像,又以争吵和互相攻著称,他们的主张往往和他们肥皂剧一般的丑闻纠缠在一起。
诺曼.梅勒在1965年提出一个观点:美国一直没有产生像托尔斯泰或者司汤达那样的伟大作家,因为在经历了“英雄的失败”之后,美国作家为自己创造了个“独立的和平环境”,满足于玩弄文字比喻,并把解释美国社会的任务留给了新闻记者。相形之下,汤姆.沃尔夫的努力弥足珍贵,虽然诺曼.梅勒并不瞧得上他的技术。
1968年,诺曼.梅勒创作了以美国五角大楼下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为主题的《夜幕下的大军》,获得当年普利策奖非虚构类奖。他在结尾写:“我们的国家,昔日她美貌无双,如今她长满天花.她怀着身孕---无人知道她是否偷了汉子.她身陷地牢,四周是无形的墙.现在可怕的分娩期到了,她开始痉挛,这痉挛会持续多久,知道的医生还没出生.她会产出什么?世界上最可怕的极权政权?还是一个属于新世界的婴儿,一个智勇双全刚强多情的孩子?”
非虚构写作兴盛时期的美国,是个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的时代。震撼一个接一个发起冲击,一个危机还没有消逝,另一个危机已成为报上头条。民权运动不断加强;有节制但绝不妥协的黑人穆斯林运动以及他们的领袖马尔科姆被杀;人们不得不认识到社会富裕与日益严重的普遍贫困化确实共存;肯尼迪在稀奇古怪的混乱情况下遇刺;牵连进越南战争中⋯⋯所有发展都超出人们的想象,步调神速,以5年为一代的历史分期法已经显得太粗疏了。这样产生了个后果——人们强烈想知道,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一边寻求解答,一边对于讲事实,有资料,可靠的,带分析性的东西产生兴趣。这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文体持乐观态度。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超级市场的伤心人》里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文章充斥的时代,我们在铺子里买文章,看杂志里的文章,在文章的缝隙里,在专栏、访问记、图片文章、记录性文字,在缩小为标题或者扩展为非小说畅销书的事实里,在真人真事的夹缝里求生存。”
“特稿组”与非虚构写作
“我让我的门前停满鸟。”
1994年,沈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式的“非虚构写作”,在媒体领域,别名叫“特稿”。“我让我的门前停满鸟”,说的是辽宁足球队一守门员技艺高超,方圆几里不仅球近不了身,门前还停满了鸟。特稿作者是个诗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话不是守门员说的,是诗人说的。在那个年头,“非虚构写作”允许一定的虚构。
199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真正从官办转向市场化经营,充满了“做中国的《时代周刊》”,“做中国的《金融时报》”,“做中国的《经济学人》”这类豪言壮语,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也是时髦之一。
1960年代,美国那帮搞“新新闻”的坏小子,坦率承认了虚荣之心——文学是“成名锦标赛”中值得信赖的武器,连华尔街的投机分子也爱文学,虽然他们决定买一本小说的原因是:看看封底的作者照片,是否比自己体面,比自己年轻,看上去比自己还要胜券在握。而且命运不是偏爱年轻而大胆的男子吗?老一代作家有的死了,比如菲茨杰拉德;有的正走下坡路,比如开始给杂志写游记的海明威。正逢杂志的黄金时期,报纸被电视冲击得喘不过气,擅长自我塑造的杂志主编跟作者一样多,他们交相呼应,全成了明星。中国年轻的媒体人向外一望,正好看见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亨特.汤普森,杜鲁门.卡波特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这也是中国媒体的新时代,我们来啦,让那些老帮菜见鬼去吧。
李海鹏眼见着中国媒体在“非虚构写作”试验中的稚嫩,荒唐,和富于勇气的冒险精神,2002年,他加入《南方周末》,2003年进入“特稿组”。早期的特稿以模仿美国为主,《普利策奖特稿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李海鹏说,其中部分只称得上“特写”——对某一新闻事件的场景还原;而非真正的“特稿”——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既有故事也有意义。
2005年左右,《南方周末》“特稿组”开始产量稳定,摆脱模仿期,主要指题材上——《小镇猪事》,央行的一次调息,蝴蝶效应到了农民的炕头上,猪肉涨价,为保证猪仔不被偷,不夭折,农民要与猪仔相拥而眠;《系统》,由网络游戏《征途》中玩家们遭遇到一个“系统”,隐喻了另一个无处不在的“系统”,“‘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声音,悄然回响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中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它的发源地美国已经望尘莫及。那个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的时代又重现了。震撼一个接一个发起冲击,一个危机还没有消逝,另一个危机已成为报上头条⋯⋯
好像一个悖论。非虚构写作小切口,大议题的特点更易容纳复杂,棘手的题材,而且它曲径深幽,晦涩难懂,像它的美国前辈实践者那样,“不好好说话”,更容易获得发表机会。可面对重大的题目,在获取信息时往往碰壁。
“牢骚没有意义,把非虚构写作的困难归到环境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给你留了缝隙,只是你做得不够好。”李海鹏说:“这事就像一个笑话:大明和小明在森林里遇到了熊,大明撒腿就跑,小明喊:你跑什么,你跑得过熊吗?大明回头:跑得过你就行。”
李海鹏这个散仙般的人物,已经回家写小说了。他是否像汤姆.沃尔夫似的,将在媒体上写“非虚构”,当作成为小说家路途中的“汽车旅馆”?还真不是,小说是他自始至终坚信要做的事,为了生计,他写了特稿,这跟他去卖北冰洋汽水是一样的;他也不是个自感铁肩担道义的人才,他只是看不得丑陋,重申常识罢了。
《南方周末》的“特稿组”锐意进取时,《读库》以一种宁静的姿态坚持另一种“非虚构写作”。
2005年,前图书策划人、媒体人老六什么不干,编辑了创刊号《读库0600》。它的宗旨是“非虚构,非学术,非专栏”,文风倡导“洁克理”,简洁,克制,理性,那些文章很长,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呈现相对静态的特点——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三十年,黄永松《汉声》编辑生涯,《浮生旧梦说隋唐》⋯⋯具有同仁杂志文艺小众的气质。
《读库》五年,证明在中国,就是小众,那也人够多的。每期《读库》发行量约3万册,在城市文艺爱好者群体内蛮有影响力。老六说:“这个时代低于一般人智商的人很多,被他们蛊惑的人也很多。但是另外一些人,那些有承诺的人还在,我们很高兴找到他们,跟这些人站在一起。”《读库》也更加拓展,不限于文艺,关注更广阔的题材。
老六对媒体有很深的厌弃——厌弃它粗劣,快速,缺乏技术规范,还张牙舞爪。也许是巧合,2010年最后几期《读库》,作者中没有一位媒体从业者。老六如同在搜罗民间观察家与民间历史书写者,那些收集抗战时期民谣的人,那些沉迷于壁画研究的人,亲自书写。最后他们与《读库》互相寻找。老六给作者规定的操作周期是“采访三个月,写作三个月”,这就是种说法,指得是一种达到精致与严谨的成本。与媒体的特稿不同,老六所坚持的非虚构记录“常态”:“在中国,仅仅常态都是宝藏,都没有被充分发掘。”当然,他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认为成本不同,其他的与《读库》不可同日而语。《读库》也并无高深的使命,如果非说要对抗什么,对抗粗糙与浮躁。
或许,非虚构写作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内心冲动。
武汉人邹波刚刚从家乡归来,带着满腔惶恐——他以为已经摆脱的“外省思想”,竟然还潜伏在身上。那是一种“居一室而知天下”的桀骜;固守于封闭环境中,相信靠直觉,常识,和神秘的玄学,就能探知世界。
毕业于中文系的邹波没有去谋份文职,而是当了警察,每天回家后趴地板上,才能让自己活过来。后来他又总在“模糊界限”——在报纸上班,一边做翻译一边负责采写;中国杂志的萌芽期,又是既会作版又能写稿的过渡型人才;他也投身于实验性的媒体非虚构写作,2010年出版合集《现实即弯路》;现在他开始了介于思想游记和调查性报道之间的写作。他的每一次界限突破,都是为了卸掉懦弱。
“武汉人天生似乎就具有完美的常识,可以不靠任何知识准备,就能评判一个抽象的事物,天,也正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当然,这也让我想起,我在云南,云南人自诩的那种天生的哲学头脑,云南诗人轻易祭出那些省内的高山大河,思想却像盆景,也许是同一回事。”在《外省思想》里他写。这玩意儿可能更普遍,普遍到中国的文人传统——缺乏实证精神,不追求确凿,更缺少社会学素养。
邹波希望借非虚构写作,达到上述的反面,避免成个“犬儒主义者”。这个词被说得那么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认为的犬儒有两种:一种对世界缺乏介入感;另一种,迅速投身世界,把自己变成个操盘手,回头再骂第一种人,”邹波说。他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些介入感,又保持着一些东西。而文学,文学也从来不该懦弱,“文学也有它的教堂,国家和军队。”
2010年冬至的时候,有两个挺热的新闻,它们都来自网络。一条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Larry King的节目停播,它是被网络干掉的。以前电视冲击了报纸,也波及杂志,现在它们都干不过网络,传统媒体作为食物链的最末端,被唱衰的命运不可避免。美国出现了一种声音: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盛行于网络,当没有大新闻发生时,传统的非虚构写作已经不灵了,人们不再有耐心花大把时间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
另一条——还有谁不在谈论《让子弹飞》吗?变着花样的影评层出不穷,其中一个说:电影高密度胡说八道的台词,正是“非虚构写作”在电影界的试验,是一次成功蒙混过关的典范。
2010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如同和平纽带,让几个圈子的人,即便他们曾经所知不多,甚至心存偏见,暂时在技术上达成和解。“非虚构写作”也像个被寄予了过分厚望的孩童,它蹒跚学步,要对抗“不信”,对抗谎言,对抗想象力根本跟不上趟的光怪陆离,对抗犬儒主义者⋯⋯它真的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刚强多情的青年吗?
本文原发于《周末画报》与《纽约时报》合办的年刊《转折点·想象2011》,作者困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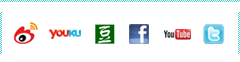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