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图说:Untitled by Ming + Hodgetts, a depiction of the Bridge inspired by "Skinner's Room" and contributed to the Visionary San Francisco Exhibition.
经过没完没了的加建,大桥仿佛珊瑚般节节长高(主要是凭着碳纤维复合物之力),桥身却始终完好如初。有些部分,原先的结构锈得不成样子,后来涂上了一层透明材料,抗拉强度比起初的钢材还高;另一些部分衬上了黑色的耐久碳纤维;还有一些用绷紧的锈铁丝缠上,多少起点加固作用。加建部分东接一块,西拼一段,说不上什么计划,但所有能想象到的技术和材料都用上了。最后,一个虽无定形,却天然浑成的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令人惊叹。
入夜,圣诞彩灯、废物利用的霓虹灯、火炬大放光明,大桥成为一块磁石,吸引着焦躁不安的人,愤懑不平的人。白天,从城区的高楼大厦里看过来,大桥使人忆起上世纪最后十年间布赖顿码头的残迹,仿佛透过开裂的民间风格万花筒看到的情景。
近来,斯金纳的髋关节虚弱得连开头20英尺的梯子都爬不了,没力气下去试乘那部由非洲仔焊到钉满铆钉的桥塔钢梁上的新电梯。但他透过地板上的活板门看过电梯了。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架线工移动升降台上的黄色塑料篮子,篮底背面装了一部马达,沿着一根涂满油脂的带齿钢轨吭哧吭哧上下,活脱脱一辆迷你版瑞士火车。斯金纳不清楚这些日子桥塔的电力供应从哪里来,但只要听到电梯马达嘎嘎作响,吊在他床边的电灯泡就会忽明忽暗。
他赞赏建造万物的人,为结构添砖加瓦的人。他赞赏盖这个房间的人,无论是谁;这个严丝合缝,栖息在风中嗡嗡作响的10层松木板盒子。房间地板是经过加压处理的双层木材, 4英寸宽,2英寸厚,竖立铺放;地板中央开了个方洞,一个优雅无比、但斯金纳早已视而不见的形态从洞口穿出,那是悬垂在大桥钢制托梁上的粗大缆索的一段。由17464根铅笔粗的钢丝绞成的缆索。
他胸前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放着一台弹出式小电视机,播着无聊的节目。电视机是姑娘弄来的。也许是偷来的。他从未打开音响。液晶屏上不停显现的图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抚慰作用,就像在水族馆中,似有似无间感觉到的运动:周围有生命。图像本身并无意义。他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说不出哪些是节目,哪些是广告。两者的区别可能早已不存在了。
他的房间5米见方,胶合板墙上刷了大约十来层白色乳胶漆,显得挺柔和。比铝箔的反射率高,他想。每条缆索17464股钢丝。事实。如今,他经常觉得自己是一道裂隙,各种事实夹缠不清,从这条裂隙挤过去,各种事实,各种面孔,彼此不相干。他的衣服挂在不成套的古董衣钩上,衣钩按相同间距钉在一面墙上。姑娘拿走了他的夹克。刘易斯皮草。大波特兰街。那条街在哪儿呢?夹克,年龄比姑娘还大。他盯着《国家地理》的照片,杂志堆在那里,挨着她白生生的光脚,脚搁在他从遗弃的办公区弄来的地毯上……哪个办公区来着?奥克兰一带?
记忆就像电视机的液晶屏幕,忽隐忽现。她端给他食物。给科尔曼2凸凹不平的红色燃气罐打气。记住把窗户开道小缝。日本罐头,拉一下拉环,就会自动加热。她问他的那些问题。谁造的大桥?大家造的。不,她说,老桥,大桥本身。旧金山,他告诉她。钢筋铁骨,优雅的缆索,把我们悬在这儿。你住这里多久了?好多年了。她用勺喂他饭,野战餐具上标着“1952”。
这是他的房间。他的床。泡沫垫子,上面铺着一张羊皮,再上面是一张床单。毯子。催化加热器。记住把窗户开道小缝。窗户是圆形的,用铅条分成好几格,每格玻璃染着不同颜色。透过中央那块牛眼似的透明黄色玻璃,能看到城区。
有时,他记起自己在盖这个房间。
大桥的骨架,它那多股钢丝绞成的筋腱,迷失在不断增生的梦想中:文身店、射击游戏厅、弹球厅、堆满湿迹漫漶的陈年成人杂志的昏暗小摊、卖香辣排骨的、无照牙托技师诊所、焰火摊、切块鱼饵贩子、投注店、寿司吧、性用品商贩、典当行、云吞馆、情人旅馆、热狗亭、墨西哥薄饼作坊、中国杂货店、烈酒铺、草药坊、正骨所、理发店、渔具店、酒吧……
都是些做生意发财的梦想,所在位置大致就是原先供汽车交通用的两层桥面。在这些店铺上方,朝着缆索桥塔的顶端,一些更为错综复杂的区域迭次延伸,那里面隐藏着更加私密的幻想,数目不详的人群居住其中,谋生手段不定,职业不明。
大桥底层下面,悬挂着用长条木板铺成的平台,中间部分塌陷下去;晴朗的日子,老人们来这里垂钓。鸥鸟打着旋,争抢丢弃的鱼饵残渣。
基尔利老旅馆的遭遇让她心中有数了:两相比较,她更喜欢大桥,而不是城区。
她初次上桥,是在雾中。她看到果蔬小贩把货物摊在毯子上,用碳化物灯和火光摇曳不定的烟熏炉照明。从北部海岸过来的农户。她自己就打那个方向来,一路经过利特尔里弗生长不良的松林,经过门多西诺县尤凯亚3曲曲弯弯、长满橡树的丘陵地带。
眼前的景象就像一个其大无比的洞穴。她死死瞪着洞口,琢磨看到的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卖小吃的手推车,汤罐冒着水汽。从奥克兰区废墟中捡来的霓虹灯,闪烁相连,渐次模糊,融化在雾中。各种各样的表面:胶合板、大理石、瓦楞塑料板、抛光黄铜、闪光装饰片、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热带硬木、镜子、维多利亚时期的蚀刻玻璃、经年海风侵蚀之下失去了光泽的铬钢—这一切之丰富、之随意,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好像一条隧道,顶上布满摇摇欲坠的棚屋,棚屋之镇斜斜地向上蜿蜒,爬上了第一座缆索桥塔。
她站了好久,看了又看,最后一咬牙,径直走进去,经过一个卖平装书的男孩,发黄的书没有封面;经过一家咖啡店,里面有只瞎眼老鹦鹉,用链子拴在金属栖枝上,啄着刚剁下来的一只鸡爪。
斯金纳正梦见一辆覆盖着藤壶4的自行车,朦胧中醒来,看见姑娘回来了。她把他的夹克挂回原先的衣钩,在那块毛边黑泡沫塑料垫子上蹲下来。
自行车。藤壶。
回忆:一个叫法斯的人一把抢过他的钓钩,把自行车高举过头,一串串巨藻从车上垂挂下来。人们哈哈大笑。法斯扛走了自行车。过后,法斯弄了个吃东西的地方,一个塞了三只凳子、一张吧台的简陋棚屋,远远伸到空中,用强力胶水和钩环固定住。他把贻贝煮熟后冷卖,外加墨西哥啤酒。自行车就挂在小小的吧台上方,墙上贴了一层又一层风景明信片。晚上,法斯蜷曲身子睡在吧台后面。一天早上,整个小店突然没了,法斯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风中晃悠的唯有一根断裂的钩环,和粘在一家理发店镀锌铁皮墙上的几根碎木片。人们赶来,在桥边站定,低头看脚趾下露出的水面。
姑娘问他饿不饿。他说不饿。问他吃过没。他说没。她打开铁皮食品柜,在罐头中搜寻。他看着她给科尔曼煤气炉打气,说把窗户开道小缝吧。圆形窗户在橡木窗框中转动。你得吃东西,她说。
她本想告诉老人去旅馆的事,但万般感受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作罢。她一勺勺喂他喝完汤,然后扶他到褪色的玫瑰花布帘子后面,上没有水箱的老旧搪瓷马桶。等他方便完毕,她从屋顶贮水箱抽出水,倒进马桶。剩下的事就交给重力了。成千条柔软的透明管子回旋交错,穿过各种建筑垂到水面上,把未经处理的污物倾泻到湾区中。
“欧洲……”她试着打开话头。
他抬头看她,嘴里含着汤。她猜他的头发以前一定是金色的。他咽下汤。“欧洲什么?”有时,如果她问他个问题,他会立刻集中注意力,就像现在这样。但此时她已经不太肯定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了。
“巴黎,”他说,但他的双眼告诉她,他又走神了。“我去过那里。伦敦也去过。大波特兰街。”他点头,志得意满的样子。“第一次贬值前……”
风叹息着吹过窗外。
她在想要不要爬到屋顶上去。通到屋顶活板门的木踏板每节2英寸厚、4英寸宽,漆成跟墙一样的白色。有一个他拿来当毛巾架用。打开门闩,用头顶起活板门就能看见屋顶,双眼正好跟一堆堆鸥鸟屎齐平。说实在的,那儿什么也没有。平平的沥青纸屋顶,两根2英寸厚、4英寸高的立柱;一根上飘着一面残破的邦联旗,另一根挂了只褪色的橙色风向袋。想到这些,她没了兴致。
等他又睡着时,她关上科尔曼,把罐里的剩汤刮出来,洗干净勺子,把汤汤水水倒进马桶,揩干罐子和汤勺,收好。她穿上高腰运动鞋,系好鞋带,然后穿上斯金纳的夹克,再看看刀子是否还别在腰带后面。
她抬起地板上的活板门,爬下去,用脚摸索到梯子头几格横档,然后把活板门拉下来关好,小心翼翼不惊醒斯金纳。她踩着梯子爬下桥塔加了铆钉的正面,来到电梯口,黄色篮子正等着载客。抬头望,只见粗大的缆索从斯金纳的房间底部穿出,又穿入一面绷得紧紧、亮晃晃的乳色塑料薄膜墙,那是间温室;卤素灯把带尖刺的植物影子投射到塑料墙上。
电梯嘎嘎作响,与她弃而不用的梯子并排,顺着桥塔表面下行,经过一片由塑料、胶合板、旧冰箱表面搪瓷钢片缝合而成的大杂烩。在厚齿钢轨末端,她爬出电梯篮子。斯金纳叫做非洲仔的那个小伙儿从窄窄的过道朝她走来,狗熊似的肩膀耸在破旧的花呢大衣下面。他手里拿了个像是仪表的东西,一个黑色盒子,拖着红色和黑色电线,线头上夹着鳄鱼夹。他的眼镜框破了,用一条银色胶带粘在一起。与她擦身而过时,他害羞地笑了一下,说了句刷子什么的。
她换乘另一部电梯,一个光秃秃的铁笼子,下到第一层桥面。她朝奥克兰方向走去,经过许多挂着二手衣物的架子,铺开的毯子上摆着各种各种作价出售的城市垃圾。有人在炸猪肉。她继续往前走,走进一片淡黄绿色的炫目荧光中。
她碰见一个叫玛丽娅·帕兹的女人。
她常常在大桥上跟人结识,但只限住在桥上的人。游客大都像惊弓之鸟,不愿跟人交谈。神经兮兮的,看他们的眼神,看他们走路的姿态,就知道了。
她跟玛丽娅·帕兹走进一家咖啡店,窗户正对海湾,曙光初现,一片灰蒙。咖啡店有老渡轮风味,暗色清漆涂在不加装饰的厚实原木上,凹痕处处;感觉好像是有人从一艘退役公交船上锯下来这么一截,捆到了这个建筑的外墙边上。奥克兰附近,一架没了机翼的747机身就派上了用场。
玛丽娅·帕兹年纪稍大些,暗蓝灰色眼睛,穿一件雅致的深色大衣,左脚踝内侧刺着一只蓝色燕子,下方绕着一串小金链。玛丽娅.帕兹抽Kools牌香烟,一支接一支,从钱包中掏出拉毛铬合金Zippo打火机点着;每次点火,一股刺鼻的苯味就会刺破咖啡和炒蛋的温和香味。
大桥上碰到人,不妨跟他们交谈。因为桥上没人不疯狂,斯金纳说;这一切疯狂之中,总能找到几个人,疯法跟你一样。
她和玛丽娅.帕兹坐下来,喝咖啡,看她抽Kools。她跟玛丽娅·帕兹说斯金纳的事。
“他多大?” 玛丽娅·帕兹问。
“挺老的。不知道多大岁数。”
“他住在头一个桥塔,缆索托梁上方?”
“对。”
“那他在这里很久了。桥塔顶端,那可不一般啊。你知道吧?”
“不知道。”
“他应该属于最早离开城区来桥上居住的那批人。”
“他们为什么来这儿?”
玛丽娅·帕兹拿着Zippo打火机,看看她。“咔嗒”一声。一股苯味。“无处可去。城区的无家可归者。大桥当时已经关闭,你知道,禁止通车,关闭三年了。”
“通车?”
玛丽娅·帕兹笑起来。“这是座桥啊,亲爱的。大家伙儿开着车来来往往,从一头到另一头。”她又笑了。“后来,车太多了,于是人们在海湾下面挖隧道。行车隧道啦,磁悬浮列车隧道啦。桥旧了,需要维修。当局关闭了大桥,可随后不久,贬值开始了,萧条。没钱按最初计划进行维修了。桥就这么闲着。然后,一天晚上,就好像有人发了信号似的,无家可归者来了。但奇就奇在压根没有这么个信号。大伙儿就那么来了。他们爬上桥两头的钢丝护网和路障;好多人爬,钢丝护网扭成一团,垮到地上。他们把混凝土路障推到海湾里。有人爬上桥塔。几十个人掉下来摔死了。但是,天亮时,他们还在这里,还在桥上,守着大桥不走,把大桥据为己有。而城区,亲爱的,”她从鼻孔中喷出两股烟,“知道全世界都在盯着呢。那些无家可归者,你瞧,不再躲藏在阴暗角落中;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这座铁家伙上头,扬言说大桥归他们了。城区不得不小心应对。日本人已经做好空运食品和医疗用品的准备。有损国格啊。来不及动用高压水枪了,不行的。他们获准呆下去。暂时获准。头一批建筑是用纸板盖的。” 玛丽娅·帕兹脸上漾出笑容。
“斯金纳呢?你觉得他那时就来了?”
“也许。如果他真像你想的那么老。你在桥上多久啦,亲爱的?”
“大概三个月吧。”
“我生在这里。” 玛丽娅·帕兹说。
城区有自己紧迫的难题。这个世纪并不好过,国家明显在走下坡路,连“国家-州”这一基本概念都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占地者获准呆下来,彻底改变了大桥的面貌。最初上桥那群人里,有企业家、天生的政治家、艺术家、能量和才华从前没机会发挥的各色男女。全世界在关注,城区暗中皱眉,桥民们开始建设,原生艺术形态的建筑诞生了。全球慈善机构的代表纷纷乘直升机飞来,接受列出工具和材料的单子。一批批高级黏合剂从日本发来。一家比利时制造商捐助了一船碳纤维房梁。一队队专业拾荒者开着破旧的平板卡车扫荡城区,满载被人弃置的建筑材料回到大桥。
大桥及其居民成了该市的主要旅游景点。硬通货,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硬通货。
初上的灯光透过窗户,透过在风中颤抖的塑料布,照着她往回走。大桥不眠,但此刻是安静时光。一辆木制小车上铺着刨冰,一个男人在上面摆放准备出售的鱼。脚下的人行道扔满口香糖纸和踩扁的香烟滤嘴。她头上什么地方,一个醉鬼在唱歌。玛丽娅.帕兹跟一个男人离开了。
她回想玛丽娅·帕兹讲的故事,竭力想象人们占领大桥那天晚上,斯金纳是什么样子。想想他那时多年轻啊,崭新的皮夹克该是贼光闪亮。她想到基尔利那家旅馆的欧洲人。硬通货。
她走到第一部电梯,那个铁笼子。她靠在铁条上,电梯沿补缀而成的隧道上行,隧道的墙壁后面,无数小小的、手工制成的空间中,隐藏着邻居们的私生活。跨出笼子,她看见穿花呢大衣的非洲仔蹲在地上,一条长长的黄色延长线顶端,亮着一只带罩的灯泡。电梯马达拆开了,散放在他周围几张新出的报纸上。他抬头看她,眼中含着歉意。“调电刷呢。”他说。
“我爬上去好了。”她登上梯子。斯金纳曾告诉她,一定要始终保持一只手、一只脚在梯子上,别想自己在什么地方,别往下看。漫长的攀爬,朝着缆索平滑的弯段。斯金纳一定爬过成千上万次了,既不数,也不想。她爬到梯子顶端,小心翼翼换到第二架梯子,较短,直通斯金纳的房间。
她从活板门钻上去。他自然还在那儿,正在睡觉。她尽量不弄出声响,但皮夹克的铬制金属件碰出叮当声,还是搅扰了他,或者传到了他梦中,因为他叫了一声,熟睡中,嗓音浊重。可能是个女人的名字,她想。肯定不是她的名字。
在斯金纳梦中,这会儿他们正往前跑,而警察,警察犹豫不决,落到了后面。头上,几架电视网络直升机在轰鸣,灯光照射下来,相机闪个不停。下起了小雨,斯金纳冰冷的手指死死抠住钢丝护网,开始往上爬。他身后爆发出一阵呐喊,盖过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电动扩音器的喊话。斯金纳爬着,窄窄的靴尖踢进护网,突然间好像变得身轻如燕,爬着,或不如说往上飘浮着,在人群的呐喊中,竭尽全力发出的嘶哑欢呼中,节节上升。他到了,到了护网顶端,那一瞬间仿佛无穷无尽。他跳下去。他是头一个。他在大桥上了,跑啊,跑啊,朝着奥克兰方向;钢丝护网在他身后坍塌,他的面颊湿漉漉一片,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
那天晚上,过后什么时候,奥克兰一边,另一个护网也倒了。两支失散的部队会师,汇成一支大军,挤成一团,挤在桥中央,手臂相拥,唱着不成调子的无词颂歌。
黎明时分,第一批攀爬者开始攀登桥塔。斯金纳在他们之中。
她正在用科尔曼煮咖啡,看见他睁开双眼。“我还以为你走了。”他说。
“散了会儿步。我哪儿也不会去的。咖啡好了。”
他微笑了,眼神再度迷离。“我正梦见……”
“梦见什么?”
“记不清了。我们在唱歌。在雨中……”
她把咖啡盛在他最喜欢的厚瓷杯中端给他,拿着杯子,喂他喝。“斯金纳,他们从城里来这儿时,你在吧?占领大桥时?”他抬头看她,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眼睛睁大了。他对着咖啡咳了几声,用手背揩揩嘴。“是啊,”他说,“是啊。在雨中。我们在唱歌。我记得……”
“是你盖的这地方吗,斯金纳?这个房间?你记得吗?”
“不,”他说,“不。有时我什么也记不起……我们爬啊。往上爬。爬得比直升机还高。我们朝直升机挥手。有些人掉了下去。到顶了。我们到了顶上……”
“然后呢?”
他微笑了。“太阳出来。我们看见了城区。”
图说:小说插图
译注:
1 田德隆区(Tenderloin),旧金山的一个城区,以脏、乱、差闻名。
2 科尔曼(Coleman),美国著名户外休闲产品制造商。
3 门多西诺(Mendocino)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县,位于旧金山湾区北部的海岸一带。县府为尤凯亚(Ukiah)。利特尔里弗(Little River)是门多西诺县的一个小社区。
4 藤壶,附着在海边岩石上的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小动物。
+ 原文《Skinner's Room》最初是为旧金山一场探讨城市未来的展览而作,修订版首次发表于1991年11月的《Omni》杂志,并与1992年荣获“轨迹奖”(Locus Award)最佳短篇提名。中文版由作者授权,黄秀铭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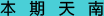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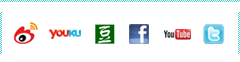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