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谁帮助我/捍卫巨人的尊严?/谁将我从死亡/从奴役中拯救?/你不是全靠自己吗/我神圣、焕发的心?/以及为上面的沉睡者/点燃青春,美好/叛逆和感恩?//我尊敬你?为什么?/你可曾减轻被压迫者/的痛苦?/你可曾平息沉沦者/的眼泪?/难道我没有造给人类/全能的时间/以及永恒的命运/我的主人以及你的?//你幻想着/我会厌恶生命/逃到野外/因为并非所有/开花的梦都结果?//我将坐在这里/以我的肖像造人/一个跟我一样的种族/受苦,哭泣/享乐,欢庆/而对你视而不见/就像我一样!
—歌德《普罗米修斯》
在《火祭》(Par le Feu)里,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oullen)重构了一个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的命运以及他所引发的革命。他同时描述了两个关于火的片段,一个是懊悔,另一个是肯定。第一幕是当穆罕默德将他的毕业证书烧毁,他生病的母亲在一边大叫﹕“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能拿到任何教书的工作!你注定要做小贩!”穆罕默德后悔了,起码在书里面我们见到他后悔了,生活越来越艰难,没有工作,警察因为他过去参加工会而针对他,坏家伙打着妹妹的主意,但自己却需要代去世的父亲挑起这头家。生活完全失去尊严。第二幕,我们见到穆罕默德自己站在街头,全身着火:一个完全的毁灭,以及重新夺回尊严的自毁。穆罕默德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自焚所带来的景象:阿拉伯春天、马德里的重夺街道、伦敦的暴乱、现在还在进行中的全球占领。
我记得去年4月在伦敦参加反对政府削减教育和福利经费,傍晚由海德公园回到Piccadilly Circus时,我看到破烂的橱窗,油漆散落四周,大批军警守在大街,战斗已经结束。但在Topshop,伦敦最为人知而又因为逃税而臭名昭著的时装店前面,一些戴着面罩的Hoddies正在烧东西。警察并没有上前阻止,交通已被警察分流,路人纷纷停下观看,没有人出声,那几乎是一片沉寂,与平时繁荣的伦敦高档购物区几乎是两个样子。在火的旁边,没有暴力,只有伤感,就好像穆罕默德烧掉自己的证书一样。游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生活是否会因此而改变?联合政府会不会只是当看不到?这两个火的意义,第一个是失望,第二个是由毁灭中重生,是几乎所有革命的历史转变的两个时刻。而也就是通过与火的沉思,我想要说一个故事,由火组成以及经火而生。
在巴黎公社期间,当提也尔(Thiers)以及他撤退到凡尔赛的军队想要重夺巴黎时,他们轰炸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也即是第一个世界博览会的地点。公社的人民随之在巴黎放火,企图阻止大军前进以及将他们分流。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唤:“巴黎要么是我们的要么便不存在”。那时巴黎公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三股思想的角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以及雅各布伯主义者,一个新的可能性正在萌芽,一个反抗第二帝国以及重建乌托邦的世界。1871年5月当巴黎沦陷之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发展了一场讲话,后来发表成《法兰西内战》,他满怀热忱地宣布:“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制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柄谷行人,当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根据这一点认为马克思其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他可能脑子里想着巴黎公社,而我们也不要忘记“联合体”其实是普鲁东—马克思的朋友与宿敌—的主要理念。“巴黎要么是我们的要么不存在”,必须在火里面延续下去。巴黎公社,一个未完成的、神秘的历史项目仍有待发掘。
1994年EZLN(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占领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以及查巴斯省的六个城镇,并向墨西哥政府宣战时,我们也见到火。火在前线上燃烧,男人和女人在那里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事实上,在那之前有另一幕的烈火,那是1983年11月17日,男女老幼到处捡木柴,然后点了个篝火,在那里EZLN正式诞生。 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我们也见到火焰处处。行动者在一大早就占领了街道和警察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企图中止世贸组织的会议。而“Black Boc”也因为这一幕而闻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或意识相近的行动者,穿着黑色帽衫和戴着面罩,开始了他们的“逛街行动”,将那些以剥削著称的店铺的橱窗打烂,将警车烧毁。在2011年的伦敦暴乱,我们也见到火,在《卫报》的图片里我们见到一名妇女在燃烧的屋子里尝试打开窗户跳下去。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暴乱时我离开了居住多年的伦敦到巴黎,几天后我回到伦敦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一名好朋友,一个芬兰社会学家,他住在Peckham,也即是暴乱的重灾区之一,那里以非洲及加勒比海的黑人区闻名,他告诉我:“在家里边吃晚饭边看BBC时,然后望出窗外,我见到附近的房子在冒烟……一切都是那么超现实。”超现实……一个尝试在梦里以及非意识中找到真实的前卫艺术运动。当其他的突尼斯人看到穆罕默德在街头自焚的时候,他们没有这种感觉吗?或者只有这种超现实的感觉才容许我们看到生活的真实?
火以及愤怒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很容易觉察,愤怒便像火一样,在寻求其毁灭性的东西,当愤怒化为行动的时候,便好像火一样不可收拾。但跟愤怒不同,火同时是隐晦的,我们并不容易发现它的形而上意义。我想要讲一个关于火的神话,那是柏拉图在《普达哥拉斯》(Protagoras)里所说的。巨人普罗米修斯有一项责任就是将不同的技术分给万物,他的兄弟厄别墨修斯自荐要做这项工作,最后由普罗米修斯检查。我们要留意厄别墨修斯的名字意为“后知后觉”,这位常常被赋予诙谐角色的巨人,将所有的技能分给万物之后,例如豹子跑得快,兔子和老鼠轻易可以钻进洞里,他发现人类站在森林的中间,赤身裸体没有羞耻地等待。他们什么技能都没有,只在那里等死。于是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的神那里偷来了火。有了火,人类可以忍受寒冷的长夜,以及吓走饥饿的狼群和老虎。有了火,人类开始他们漫长的文明,一个关于技术的历史。 普罗米修斯所受的惩罚是,他被锁在悬崖,每天鹰群将他的肝脏吃掉,晚上新的肝脏又会长出来准备白天的折磨。
在其它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描述里,他不但是偷火者,而且他创造了人类。 所以歌德的诗《普罗米修斯》描述了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对立,“我尊敬你?为什么?你可曾减轻被压迫者的痛苦?你可曾平息沉沦者的眼泪?……我将坐在这里,以我的肖像造人, 一个跟我一样的种族,受苦,哭泣,享乐,欢庆,而对你视而不见,就像我一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不是由神所给予的,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及重新创造的。反某个政府、反全球化并不是说人们不支持世界的大一统,而是另一个全球化,那里没有剥削,没有跨国界的奴隶(移民工人、非法劳工),没有种族、性别歧视。
没有火的人类是没有尊严的动物,他只是一个“祼命”(bare life),裸站在森林里完全没有羞耻。火是人类自觉羞耻的条件,也是人类离开神话源头的条件。同时人类羞耻的历史开始了,而吊诡的是这种羞耻也在火中毁灭。在人类抗争的历史上,我们发现毁灭机器、工厂、汽车作为反抗某些政府以及资本主义所强加给我们的羞耻并非巧合。另一个法国作家斯蒂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一个柏林人同时也是一个巴黎人,他参与了法国抵抗纳粹的战争,战后担任法国的联合国代表参与“世界人权声明”(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我们要留意“universal”这个“普世的”意义并没有在中文的“世界”一字中表达出来。Hessel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小书在法国成为大热,并且被翻译为12种文字。这本小书的书名叫《愤怒吧!》(Indignez vous!)。据说这本书在西班牙有很大的回响,那些占领街道的行动者称他们自己为“愤怒者”(Indignados),但这个西班牙词语依然保留着拉丁字源﹕“失去尊严”。虽然,我们可以猜想另一个源头是Zapatista,一个以“重夺尊严”为目的的墨西哥原住民运动。但到底什么是尊严,如果我们要讲“羞辱”或“去尊严化”的话?
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设定了一些伦理上的承诺(commitment)。我必须承诺有一个超越(transcendence)叫作人类尊严,我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平等的人类。我没有想要写一个关于伦理的大道理。我在哲学和政治的承诺一直都是关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以及怎样与其他人相处?我与安那其主义走得很近,因为我认同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及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分析,前者我与之分享着友谊以及有趣的讨论,后者的著作让我多年来对德国及法国哲学的研究与我的政治承诺联结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安那其主义是一种伦理,它强调“他者”以及“共同体/社区”的形而上问题,它并非普遍以为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纲领”。我也必须说我是一个哲学思考者,并不是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我只能在这些简单的问题上踯躅。通过讲述关于火的故事,我想要提供一些理论性的、历史性的片断,可以让我们理解当前的景况以及可能的转变。火创造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通道,这个“重夺”并不是手段(mean)或者目的(end),而同时是两者。
羞 辱
抗争底下的动力是愤怒。我们,抗争运动的老兵以及自由法国的战士,我们呼吁年轻的一代去活出以及传播抗争的精神以及理念。我们告诉他们﹕接手吧,愤怒者、受屈辱者!政治、经济、知识的责任,以及社会的整体性不应该被解散;也不要畏惧金融市场的国际性独裁,他们正威胁着和平和民主。
—斯蒂凡纳· 埃塞尔《愤怒吧!》
今天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是一个最明显而又最少被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随着新的科技、医学的发展,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比以前更好的状态。虽然那边厢有全球暖化,但很多人都相信那只是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周期性地缩短而已。至少人比以前活得更长。那是真的吗?犬儒主义者轻易地回答:“发展中国家会越来越富有,不是吗?中国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吗,那里人们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犬儒主义者会问:“怎样?”他们很明显不想加入任何的辩论,然后回到洞穴里发现现实是最好的状况。人类状况在全球性的劳工、土地剥削以及消费主义控制欲望之下已到了一个临界点。近来全球性的占领运动以及社会运动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马克思一早就已经在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运作中解释了第一个“羞辱”的问题。因为矿产的发现,农民失去了土地,最后要到工厂工作。工匠们世世代代所传下来的技能原本足够他们维生,但是因为机械化大生产,他们的技能已沦为过时,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生活而加入工厂的工作。劳工(labour power) 仅成为交换价值,以换得面包和牛奶。在工厂里,他们要跟着机器的节奏,将他们自主的身体交给机器的自动化,也即是他们成为被动的、提供能量的个体。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视这种“知识的流失”为“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过程。中文将“proletariat”译成“无产阶级”或“贫民”其实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proletarianization”更像是“废人化”。斯蒂格勒的解读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异,他们不少人至今仍然视“劳动阶级”为“proletariat”。斯蒂格勒视“废人”为那些失去知道怎样做(know-how)的知识(savoir faire)的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savoir vivre)。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状况的第一个灾难性结果,它远比经济意义上的危机—累积的危机—更加严重。而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几乎控制了所有不同行业的生产。
但资本主义并不能松懈下来,它必须制造消费,否则累积的危机只会继续下去,而资本的流通也将会缓慢下来。当工人无法在工厂里获得生活的知识(savoir vivre),他们只有在空闲的时间去创造一些另外的东西,这为资本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可操控空间。在20世纪之交,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将精神分析引进了营销技巧,并将商品经济和“利比多经济”(libido economy)结合。那些常常嘲笑将广告“心理分析化”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憎恨一切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人如果知道其实伯内斯是弗洛依德的外甥之后可能会稍微改变看法。伯内斯雇用了一些心理分析师加入营销策略的设计。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推广香烟产业,那时美国吸烟的人口主要是男性,女性并不视吸烟为一个有趣的东西。伯内斯于是雇用了一批女明星在公众地方吸烟,吸烟因此成为了一种性感的东西,挑动着男女之间的欲望,这也是商品与利比多投资的结合。一年之后,香烟的销量增加一倍。今天我们见到的例子当然不只是香烟,而是所有的商品。今天我们见到的是身体与资本给合的一个个新的线路(circuit),先是劳动力的剥削;其二是通过操纵工人的欲望而加快流通的过程。
这些线路在“平等、尊严”等虚构的牌匾下被制造,因为人有工作的自由,人的尊严可以由他的财富、地位所建立,所以人们需要构买LV、Gucci、跑车、豪宅等等。这些自由意识形态底下的价值如“平等、自由、尊严”很容易地被廉价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资本家利用去掩饰他们剥削的乌托邦。在撒切尔以及里根的时代,这些线路完全失控。新自由主义将“自由”(liberty)的概念转换成“不负责任”,他们将战场完全交给了资本家,然后一方面称自己为“小政府”,另一方面制订新的政策以配合资本的扩张。人类赖以生活的“公有资源”(commons)也逐渐被“私有化”所侵蚀。“公有资源”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public),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公有资源”其实是属于政府的。“公有资源”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例如森林、水、空气等;另一方面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自然资源以及知识产权的私有化加快了商品化的过程,同时将许多人的谋生机会完全剥夺。萨帕塔(Zapatista)运动的一个起因就是Lacandon丛林的私有化,而导致正面的冲突。
在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我们见到新的线路,工资不仅跟消费而且跟金融市场挂钩。例如知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将美国退休基金(pension fund)视为一个“沉默革命”(silent revolution),因为每个人一开始工作便要开始投资基金,而当银行的利息越来越低的时候,积蓄便会贬值,最后工人如果不投资便会一直蚀钱。也即是说“多劳多得”这个原则已经不复存在,投资的原则并不是“多劳多得”而是“投机”。在“投机”背后是不同的贸易方法,例如我们熟知的对冲基金,或者属于业内专业知识的算法贸易、噪音贸易,这些都是交易员以及投资者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系统,最后制造了一个脆弱的债务系统,准备它的随时破灭。所有这些线路背后都是一个个的“革命”,例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1980年代美国的“沉默革命”,英国的“保守革命”,但这些资本主义“革命”最后所造成的灾难并没有令人们有改变这个系统的想法;而另一边厢,共产主义经过几次的失败之后,它已被广泛地视为一个永远不可以尝试的计划。这些灾难并不是等一个走了再来一个,而是在我们的年代并存。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或者被迫廉价卖出去,最后他们要改变生活模式去成为城市廉价的劳工,以购买面包—他们在过去可以自己生产的东西。在富士康,工人就好像动物一样被呼喝,分工将所有的工序都变成极其微小的动作,工人最后只是机器。消费主义将城市变成荧光屏以及广告海报的空间,那里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也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知识。而“投机”更没有他们的份儿,这便是“savoir faire”的完全丧失,最后工人要自杀,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怎样去生活。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1994年发起的起义针对的正是人类尊严的完全丧失,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喊﹕“ ¡Ya Basta!”(够了)。人类尊严是最困难的形而上问题,几乎没有答案。但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就好像圣奥古斯汀回答“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一样﹕“如果没有人问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我想要向问我的人解释,我并不知道。”时间的神秘性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尝试将它的无法解答性联系到存在本身﹕“存在(Sein)到底是什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存在的沉思中去发现尊严的不可解答性。或者在以下这个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La Palabra发表的声明,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相关性:
那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折磨让我们发声,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语言里有真理,但我们不只知道我们的舌头有痛苦和折磨,我们还知道我们的心里依然有希望。我们跟自己说话,我们洞察自己,我们回顾自己的历史﹕我们见到我们的祖父在挣扎,我们见到我们的父亲心中的愤怒,我们见到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拿走,我们有最宝贵的东西,它使我们生活下去,使我们的踏步在植物和动物之上,使石头奠基在我们脚下。而令人羞愧的莫过于忘了它,我们见到尊严让人再次成为人,而尊严将回到我们心中,我们是新生的,而死去的,我们所死去的,看到我们重生的时候,他们会再次呼唤我们,去捍卫尊严,去挣扎。
内 战
团结人类的基本元素并不是身体—个体而是生活方法(la forme de vie)。
内战是生活方法的自由的游戏,是他们共存的原则。
“战”(Guerre),因为在每个生活方法之间的独特游戏里,在残酷对立的可能性里,所使用的暴力不能被还原。
“内”(Civile),因为生活方法并不像国家一样因为人口和领土而发生冲突,而是好像党派一样,因为这个词是直到国家的出现才产生,也即是说,如果需要精确描述的话,好像党派的战争机器。
—提昆《内战导论》
“和平是战争延续的其它方式”,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一早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和平掩饰着内战,并且用军事力量去执行警察秩序。在警察秩序里面,只有两个可能性﹕听命令做事,或者用金钱去腐败他们。内战背后,和平已失去意义。而第一个革命性的内战的称号或者要给予巴黎公社。城市里的空间被占领以及重新安排去迎接一个社会主义蓝图。马克思写道:“在公社里,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失败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前景失败,柄谷行人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公社的成员并没有顾及普鲁士的军队。卑斯麦在提也尔的要求下,释放了几万名囚犯让他们加入军队。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滑稽的一幕,军队要由警察监督以防罪案发生。这也预言着这种意义上的内战并不可能取得世界性革命,因为“国家与国家是相对存在的” 。然而巴黎公社留给了后人很多希望,今天回头看它依然像个神话一样,美好得令人要去想象新的可能性。一种生活方法,正如Tiqqun所说的。
第二个革命性的内战是西班牙内战 。“最接近安那其共产主义”,一位朋友不断地向我重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1929年当华尔街崩盘的时候,西班牙仍是一个农业国家,70%的人口仍然靠土地生活,而农业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纷纷增加关税,结果西班牙被迫要进行转型—工业化。工人在CNT(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全国劳工联盟)的带领下进行起义,要留意的是CNT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工会,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它都没有好好地把握机会。这也是为什么CNT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计划,然而这也变成一个最有利的地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工人和农民都加入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在他的《西班牙内战与加特兰尼亚》里描述:“(他们)的武装比起英格兰公立学校里的训练官还不如,他们的来福枪往往在打出五发子弹之后枪膛便塞住了;几乎50人才有一把机关枪,而30人轮流用一把手枪。”政府将良好的枪械收起来,让15岁的孩子拿着有40年历史的来福枪上阵,因为政府害怕一场革命远甚于法西斯。在那个时候,CNT几乎发展了一个未来的安那其计划,如果实现的话,那将证明对国家的坚持是最无谓的保守行为。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未来是可以想象的。那里的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以及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自我组织是人类的强项,并不一定要规划。在西班牙内战的前段,在农业以及工业出现了很多的“集体化”,但我们要留意这些集体化并不是苏联的那种强制性的“集体主义”,而是几个农民负责一小块土地,然后由代表向集体交涉,包括肥料、灌溉等事务。那些不愿意加入集体的人士可以得到在不雇人的情况下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以杜绝地主的出现)。这种集体化不只出现在农业上,工业及服务业也如是,CNT的电车工人分部在巴塞罗那一个简单的例子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就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CNT的电车工人分部占领了电车的控制权,电车畅快地在巴塞罗那的街道奔走,与1936年的1800万人次相比,1937年电车载客的人次高达5000万。我很喜欢大卫·格雷伯所说的,如果你视他人为小孩,他们不会表现得像大人。在香港响应华尔街的占领活动时,一名电台记者向我投诉,那些占领者只会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好处”。我其实不知道怎样回答,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信念,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便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便没有新科技,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我想象的刚刚相反。我能想象一些真的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科技,一些工程师、哲学家、人类学家联手,可以开发出对人类危害少、而又真的实用的东西。事实上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很多技术人员、科学家自动加入农民的集体帮他们发展新的方法种植。在“竞争”的名义下,许多癌症病人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去获得几片药,它的制作费用可能只是售价的百分之一;在“竞争”的名义下,我们买的每个小工具(gadget)的寿命越来越短。
巴黎公社消失了,CNT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败,资本家和法西斯携手合作,但背后最大力的破坏者或许是斯大林,因为只有斯大林主义者才能获得优良的枪支,CNT的成员只能上前线送死,柄谷行人关于巴黎公社的分析用在西班牙内战也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今天我们所谓的内战,最后都只是变成美国式的改革而已。但内战并没有因此消失,如Tiqqun所说的,我们要将内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层次。内战可以泛指国家内部所有的抗争,人民和国家以及资本的对立制造了无止境的战争,反抗并不只是上街游行,而是更有组织的活动。内战将以新的形式出现,而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暴力”这个指控。同时内战并不再局限于国内,全球化之下,跨国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类似古罗马似的“帝国”(Empire)。这是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观点,在资本和国家的结合中,国家的主权相对地被削弱。这个观点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小心对待 。但我们可以采用最常见的理解,资本和国家的辩证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内战,并不再以国界划分,而是全球化的。如果我们观察近十几年来的抗争,所响应的已不再是国内的行动者,而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占领运动的例子是不证自明。
占 领
要有更多的开放空间可以容许军队以及大炮的流通以抵制任何起义是第二帝国要重新发展市容的原本目的。但是最后目的除了警察的考虑之外,豪斯曼的巴黎是一个由白痴建立的城市,只有噪音和愤怒,毫无意义。今天,都市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的问题是逐渐增加的车辆的流通。但并不是说不能想象未来的都市主义既可以应用于毁灭,也可以有用处,如果我们考虑可以带来更多的心理地理学的机会的话。
—居伊·德波《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论》
占领常常是去重夺权力与空间。所以巴黎公社、西班牙内战、萨帕塔运动都有很强烈的占领元素﹕工厂、土地、建筑物等等,但占领的规模似乎越来越小。近代的战争大力地提升了军队以及警察的作战、情报能力,让他们更好地为政府以及资本家服务,任何起义都会迅速地被以反恐为名消灭。我们的时代,任何想要从政府和资本家夺回尊严的努力都有很大机会成为恐怖主义者。例如Tiqqun在2009年被控在法国的小镇Tacnac炸掉火车的铁轨,事实上警方毫无证据,而他们逮捕Tiqqun九个成员的时候,理由是这班人没有使用手提电话,十分可疑。
在1968年,巴黎和史特拉斯堡的学生尝试去成立他们的军事基地,当然最后以失败收场 。1970年代初,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运动—后来发展成为“自治主义运动”,并且给我们贡献了当今重要的思想家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和比弗(Franco “Bifo” Breardi)—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要求“不工作”。“不工作”的意思并不是说坐着等国家养,而是不要成为以劳力换取工资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异化的个体。这个运动并没有占领整个意大利,许多人入狱,例如奈格里便逃亡到法国,后来回意大利完成他的刑期。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1994年1月占领了Chapatas的几个镇的时候,政府立刻回以火力,最后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丛林。军队和警察从没有给人们民主,只是在维持着某种狭义上的民主以巩固政府的地位以及方便资本的流通。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终也只有改变战术。马科斯(Marcos),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副司令,一个蒙着面但据说是白人教授的神秘人在1994年撤退回丛林后的一个访问提出﹕“我们说‘让我们摧毁这个国家(state),这个国家系统。让我们打开这个空间以及让人们接触这些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民主、自由以及正义,因为只有这些物质的条件被满足,人们才有机会加入国度(country)的政治生活。”
我逐渐去想我们前面提及的内战,以生活方法去对抗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作为占领的目的。其中一个理论来源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国际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 International)的代表人物。巴黎在第二帝国的改建下几乎完全改变。路易·波那巴,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既能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农民承诺一个光明的未来,邀请豪斯曼重新设计巴黎。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士绅化”(gentrification),小而窄的街巷被拆毁,宏伟的建筑取代了矮小的楼房。近200米宽的林荫大道可以方便警察及军队尽快平息动乱。巴黎,19世纪欧洲的首都,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述的,整个“士绅化” 的过程根本上是一个 幻景(fantasmagorie),资产阶级的品味笼罩着城市,住宅区也像傅立叶(Fourier)想象的变成商场(galerie)一样 。本雅明的策略是去发明一种叫“都市漫游者”(flâneur) 的身份,他从波德莱尔的忧郁和被商场所侵占的小街中找到灵感。今天“都市漫游者”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那是本雅明没办法看到的,一方面“都市漫游者”仍然代表着对都市化的反抗,一方面它又已成为都市化的一部分。当我们想一想那一片片崛起的艺术区以及将街头艺术规范化、学院化的过程时,这几乎是昭然若揭的。
德波可能也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景观”(Spectacle)的概念,因为“景观”远离个人化的政治,也即是它从“都市漫游者”的身份移到造成这种身份的条件。德波的“景观”并不仅是影像、符号,而且是其后抽象化的社会关系。情境主义者的主张是去创造情景,然后重新回复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暂时中止(suspend)“景观”对日常生活的角色和功用。德波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意为一种新的地图可以容许我们用另类的方式去探索都市。例如,情境主义者提出一个叫“漂移”(dérive)的技巧,参加者以团队的方式一起漫无目的地根据他们的心理以及情绪状态在城市里游荡。它把主体暂时地带回了自己的空间,并减少被他人事先计划的路线影响。情境主义者的策略制造了一种新的美学,它和主体处于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也是它与“都市漫游者”的美学不同的地方。
但占领并不只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在空间上它改变了对街道以及空间的诠释,同时也改变了街道以及公共空间的功能。占领同时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是一个重夺属于“我”以及“我们”的时间的方法,一个不由“景观”所主导的共同体。我常常提出要在分析政治经济的同时,探索一个形而上的批判。政治经济十分重要,但其背后的形而上意义也需要探究。资本主义如我们上面提及,生产了很多空幻的“善”,我们需要去暴露他们的局限。不同的线路,如生产、消费、投资花费了所有的时间,人最后从事的已不是人的活动,而是成为动物。那些将人类社会关系抽象化的“景观”,同时将人们的“意向”(intentionality)以及注意力变得更有生产力 。但所谓的更有生产力只是购买多些商品而已。
欧洲和北美的“占屋运动”(Squatting)是反对政府土地私有化政策以及抵制无止境的发展、重建的行动,在我眼中他们是“反景观”的空间政治。但在市区以外,还有许多被“景观”所遮蔽的真相。很多非洲、南美洲、亚洲的人口还是担心着土地以及粮食。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自足,而是他们的资源被剥夺,而政府又没有提供任何支持。马科斯在一个访问中谈到他感受最深的事件,便是一个小女孩在他的怀中死去。那个小女孩晚上六时开始发烧,十时去世,而当时整个地区并没有任何药物(事实上那里大部分地区没有水没有电)。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只属于马科斯的故事,它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我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去志愿帮助萨帕塔运动,她告诉我她讨厌任何军队,但在那里她说她深深感受到为什么军队是必需的,因为人们真的需要战斗,要不然就只有等死。
计 划
有什么计划(programme)?
这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常问的问题。而最诚实的答案可能是“没有计划”。要让一个改变发生,而不陷入旧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它必须勇敢地宣称计划必须由人民自己想象。CNT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自我组织以及互相信任的重要性。萨帕塔运动示范民主并不是最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民主和自治在抗争的过程中产生。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口号并不是为人民而战,而是与人民一起并肩作战。这与任何政党政治都不会兼容,特别是那些以制造明星政客为目的的团体。这便是我在一开始说的伦理。萨帕塔运动是不是无政府主义重要吗? 今天执著于“主义”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安那其并不是一个社会政策,也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国家,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尊严非常重要的伦理,而谁又能知道哪个计划是最好的,最恒久的呢?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今天世界的理解依然是相当重要的。
我不能给出一个计划,但我想要建议一个没有计划的计划,意思是一个没有特别目的的计划,但是视本身为目的。例如萨帕塔运动便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尝试将组织民主化。但最重要的是去行动(act out),去组织。抗争永远都是在个人的能力之内以及意愿之下,我们在历史中学习了无数类型的抗争,从军事抗争到社区建立。在1999年西雅图运动之后,人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抗争方法去扰乱警民对峙时惯常的逻辑。这些反抗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在西雅图运动,“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在他们的声明中指出﹕
是时候在世界的其它部分,去提高那些全球化集团的社会和政治代价,他们正在制造毁灭以及混乱。人们有很好的机会去用街头剧场—艺术、舞蹈、巨型人偶、涂鸦以及剧场—以及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去简化以及戏剧化全球化集团的问题,以及发展和散布新的、有创意的抗争。这将可以帮助推动美国和加拿大的群众运动用以挑战全球化资本以及促成激进的改变和社会革命。
这些都是每个人可以做的,如果他或她想要为尊严而战。人们可以走上街头穿得像个米其林人一样,在警察前面跳来跳去;人们可以每天都在街头举行嘉年华似的聚会。这些在某种形式上都是占领,去重新诠释空间以及赋予主权。但这样子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景观”,争取传媒的30秒报道?或好像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一样,今天只能成为怀旧的消费品?资本主义的市场现实主义几乎可以吸纳任何反对的声音并将其变成自身的生产力,这就是我刚刚提出的主体以及美学处于一种辩证关系的原因,新的行动是一个个扬弃(aufheben)的过程,它并不只是一些可以被重复的技术。但我想要提出的另一个计划是﹕去自我组织社区或公社。通过组成社区,人们可以开始避开和破坏资本及国家共同缔造的线路﹕生产的线路,流通(消费)的线路,以及投资(金融)的线路。开源计划(open source)以及它之前的自由软件运动示范了另一种生产的方法﹕它不是基于被命令而是基于奉献。今天“开源”这个词开始被微软、谷歌等集团采纳—另一个辩证的过程—但还有千千万万的开源软件、硬件计划。开源社区建立了一种新的利比多投资,它不再是被商品所控制,例如越来越频密的更新,也不是投资在一个对象上,它可以对很多人有用。
我今年1月份去探访伦敦利物浦街的占领社区时(他们占领了一个银行空置了的办公大楼),我被一名律师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他是专为金融业的罪犯辩护的律师,所以他口口声声称他们为“畜牲”(bastards)。他提倡去创造一个个新的、本地的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将所有的交易都电子化,加入一连串的元数据(metadata),投资者可以监察他们的钱到底去了哪 里,而且可以用有限的信用在区内互助。姑且勿论这些提议有多成熟,对于现实的批判有多深刻,但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建议,它们并不是不可能被实现,它们只是需要那些沉迷于开发商用系统的程序员的响应。我想这种社区的建立,采用的不是“否定”(Negation),而是去忽视当前的系统,当它们不存在,同时去开发新的线路。从这一点上,我相信新的技术、新的欲望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可以被发展出来。我也相信德波所提倡的艺术和激进政治的结合可以被实现。如果“士绅化”今天是用艺术和设计去改造社区的经济,那或者我们可以用社区经济去改变“士绅化”所带来的“艺术”。
今天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区”的解释,它到底是什么?当Facebook也在声称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社区时,它只是把社区理解成一大批个体聚合在一起而已。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的学科已经展示给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社区的意义。例如大卫·格雷伯几乎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都在提倡“礼物经济”。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外甥(另一个外甥!)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礼物》(Le don)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挑战了经济学上常见的预设:(1)经济的起源是以物易物;(2)经济是基于物资的短缺;(3)交易都是个人化的。早在莫斯之前,已经有两名著名的人类学家书写过“礼物经济”,他们分别是研究太平洋西北区域,特别是英属哥伦比亚的Kwakiutl部族的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研究Melanesia的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他们书写的民族志里,“礼物经济”可以简单描述为:人们以部落的形式赠予礼物,而收到礼物的人则有义务回赠。礼物赠予并不只是因为要显示慷慨,例如在婚礼、葬礼时的行为,而是如莫斯所说的“整体的社会现实”。这些大型的互赠节日叫“Potlatch”,有时候赠予并不只是出于友谊,有时是敌对,要看哪一方可以赠予得多一点。这种“礼物经济”背后的意义是,另一种物品流通是可能的,而在给予和接收的过程中,一种新的价值可以借此产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残留着许多“礼物经济”的痕迹,问题是怎样去重新发现它们,并应用到社区里。
另一方面,在占领过程中许多团体都采用共识民主,这是安那其们用来决策的方法,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一个人无法被说服决议都无法通过;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将每个人计算在内。这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去重新夺得尊严的维度。未来在前面,每个想要改变的人都要回望,在自己身上找到那些被短路了的线路,去重新发现被“景观”强占了的生活。所以必须占领任何地方,占领所有的东西,去重新建立新的关系和新的线路。当我在香港参与占领运动的时候,我曾提出占领公园里的花坛,这听起来是个很可笑的建议。但当我们将种子播在所谓公共空间的花坛上时,园丁便会将发了芽的种子除掉,我们便会进入一个与权力对峙的局面﹕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觉察的权力架构。但到底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公有资源”?当所有的东西都归入管理之内,然后经由政府和资本家的管理协议(protocol)运作,我们只能永远为他们服务。但当我们开始去思考“公有资源”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些种子慢慢地会变成为另一种种子,它们或可以打开另一道裂缝。要留意的是,我没有说社区将局限于细小的群体,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一些大型的工业也可以由社区式的自我组织来维持。
我以“火”开始这篇文章,我也将以“火”结束。执笔至此,刚刚传来了雅典市中心大火的消息,《纽约时报》则在埋怨安那其,因为这活像19世纪的反资产阶级运动。历史在不断地重演,在一切系统性暴力之下,他们其实是一个个叹息和失望,并不是什么“快乐抗争”而是无比的沉痛。但我想提另一种“火”,它不是失望也不是毁灭,而是欲望和慷慨。从巴黎公社到西班牙内战,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1994年的萨帕塔运动,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充满革命热情的2010年,以及中间那些我们不能一一罗列的各种抗争运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类改变这个世界的欲望﹕一个个自由人,重夺尊严,或者如马克思想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又或者马科斯的描述更加实在,像孩子一样,他们可以随时玩耍,天真地生活。但今天的孩子没有这种生活,他们要工作,他们要为自己将来赚大钱打算。成为孩子,也是去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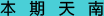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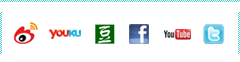

评论